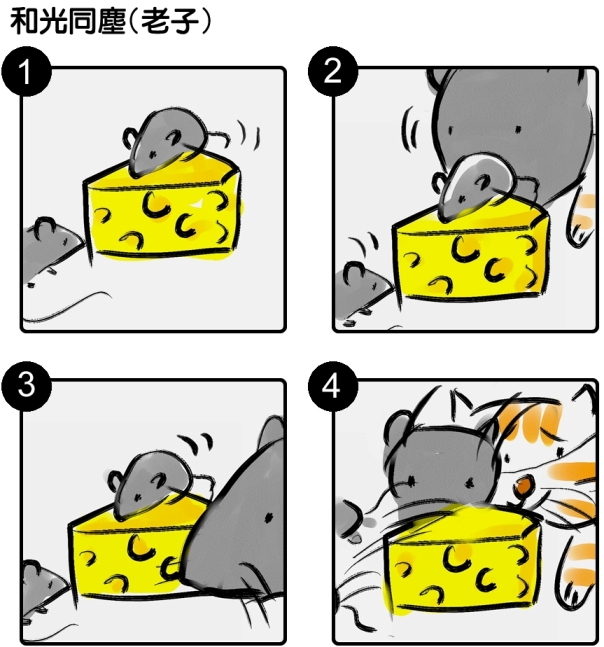道教新論
 |
|
序
我對宗敎事務夙感興趣。蓋性喜幽奇,博涉多方,輒於此寄寓遐思也。但並不只是單純的宗敎感情導引著我去接近宗敎、試圖理解宗敎。而是基於對中國文化的總體關懷,使得我必然要注意到儒家及儒家以外的宗敎狀況。
民國六十七年左右,友人林明峪整理了《禪機》《媽祖傳說》《台灣民間禁忌》等書,我曾參與其研究過程,對佛敎和民間信仰做了些初步的探討,零零碎碎寫了點文章。其後我又花了一些氣力研究我國的宗廟制度、祖先崇拜、宗族會社等。並試圖通過天命思想去鈎勒中國小說史的嬗變、利用佛家三性說去處理宋代詩學理論及「學詩如參禪」的問題、由儒佛對抗關係上去理解唐代孔穎達所編修的《五經正義》……。這些硏究,在發表時多少均引起過一些爭議,因爲取徑略異於時賢,亦非純宗敎之研究,乃是依我對文化史之研究方法和分期的整體看法來的。我的文化史研究,主要是想觀察一個文化體在時間和空間的延展中,如何與自覺的價値意識互相感應,而帶出意義的追求及處理事務時的不同取向。宗敎所涉及的,正是一群人的終極信念與存在安頓之問題,由這個地方來審察其意義取向及性質,當然最爲眞確。因此我較喜歡由此切入,撥開表像,直探意義之核。
民國七十八年,我在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籌辦了第一屆中華民族宗敎國際學術研討會。其後道敎協會成立中華道敎學院,亦邀我任職敎務,並講授「道敎文獻選讀」。今年四月,我又於雲南籌辦海峽兩岸中華民族宗敎與文化硏討會;並與靈鷲山般若文敎基金會合作,創辦國際佛學研究中心。這些事務,使我與宗敎界有更廣泛的接觸,也更直接地進行了宗敎研
究。
我家世原本與道敎有些淵源,家伯父龔乾升先生,在《歷代張天師傳•序》中提到:「餘與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眞人,自韶關遇合,至浮海入台,時聆妙緖,旣上書內政部以維道統,復翊創道敎會以振玄風。交契苔芩,誼聯蘭譜」云云,即指其事。家堂兄龔群先生,現亦仍任嗣漢天師府秘書長,且辦有《道敎文化》雜誌。道敎之科儀掌故,我因熏習日久,故亦略有所知。藉此機緣,遂通讀《道藏》,並因往遊大陸之機會,參訪宮觀,檢輯資料,以與昔日所曾思慮者相印發。
這些印發,自有助於我建立統観的文化史解釋體系,但那些問題比較複雜,不擬在此論敍。在此謹專就宗敎研究的部份,略抒管見。
我以爲民國以來知識份子在理性精神的發展中,形成了一種偏見:高舉理性、批判宗敎等非理性事務。以致對宗敎異常隔膜。宗敎硏究遂難以進行。幸而佛敎界尙有楊仁山以來諸名家,闡述義理、整理文獻、積極與世界佛學哲學界對話,故仍有不少成績。道敎及一般通俗敎派便寂寥得很了。而且,我們自己固然乏善可陳,就是國外的研究也未必靠得住。
倘不嫌我冒犯權威,則我願舉個例子來說明。
《世界宗敎資料》一九八五第三期鄭天星〈中國民間秘密宗敎硏究在國外〉曾說:「日本學者通常把中國民間秘密宗敎硏究稱做中國宗敎結社研究,或簡稱白蓮敎研究。」在這種
研究中,野口鐵郞先生的著作,無疑是極爲重要的。他《中國宗敎結社史研究序章——とくに白蓮敎史を中心とレに研究史的動向》、《明代宗教結社的經濟活動活動》、《白蓮敎運動理解への試論》等文,皆為治明淸秘密宗教及會社史者所不能不讀之作。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淡江大學舉辦「第二屆中國政敎關係國際學術會議」,野口鐵郞所提「明淸時代的正敎與邪教」一文,殆爲先生研究明淸秘密宗教的總提綱,論旨可以涵括他所寫過的專著。因此,我想即以這篇文章來檢討一下有關明淸宗教結社研究的方法問題。
野口鐵郞此文先說明所謂邪敎的大致狀況,然後討論邪教與正敎的衝突。他認為「邪教」起於白蓮,倡言彌勒下生,宣傳否定現世王權的救世主降臨預言;配合著世人對社會現實的不満,以及均產的願望、長生富貴的心理期盼,故往往起事反亂或革命,與政府不妥協。當然,此類宗教常模擬世俗王權,分封官職。但基本上它們是與政權相衝突的。他們夜聚曉散,活動方式極爲隱密;他們禮拜聚會時,可能也因民衆有性平等或性共有的希求,而有男女混雜之現象。這些都直接衝擊了官憲體制和社會道德倫理秩序。其教徒奉獻,亦可能影響政府稅收。所以政府經常要査禁剿除之。
但政府並不如此對待「正教」,原因何在?野口鐵郞認爲:中國古代事實上是個家族道德擴大而成的國家道德體系,所以中國的宗教也是皇權一元化的宗教祭禮型態。國家奉行儒敎的典禮祭祀,如祭郊社、封禪等。凡不爲此一中央權力承認的地方民間祭祀,皆稱爲「淫祠」「邪教」。因此,國家權力—宗教—社會倫理秩序是一體的。外來或新興宗教,必須與政權妥協,如道敎佛敎,在明清朝都甘心居於政權的從屬位置,由國家發給度牒、納入管理,並利用經卷及法會替王者祈福。另外,對民間供奉的無害於政權之神祇,王朝也可能予以承認,且授予封號。換句話說,民間新興的宗敎倘若要獲得朝廷的承認,即須經由以上這類途徑,否則便被判定爲邪敎,會遭到查剿,成爲被迫害的對象。
這種講法極有見地,特別是指出了國家權力與祭祀權的關係。國家政權往往不只是政治權力而已,同時也掌握了敎化權和祭祀權。民間新興宗敎若冒犯或危及此一政治—敎化—祭祀一元化體系,必然要受到壓制。
但利用這個觀點來處理明淸宗敎結社也是危險的,因爲此說至爲狹隘。明淸時期新興的民間地方敎派敎團,眞正涉及反亂革命或擁有反政權之政治傾向者,其實並無如此之多。現在的研究,所根據的大多是史冊中的敎匪文獻。依據這些材料,必然使我們的眼光只集中在政敎關係上,而且只集中在政敎衝突面。所以得出了這樣一個印象。彷彿秘密宗敎都是否定王權的團體,執政者也刻意鎭壓此類敎派。卻未注意到:歷史上、特別是官文書及反敎人士所批判的敎團,不及當時存在者的十分之一。那些未被批判的敎團,大多並不反對政權。即使是被點名批判者,大多也未主張對抗皇權。他們被批判,往往是因爲受到誣陷或敎外人士之猜疑誤會使然。因此不是單純的「國家權力遭到挑戰」說,便能解釋這個複雜的問題。對所使用的材料與觀點,我們都有必要進一歩反省。
正如他所使用的材料偏重於官方敎匪文獻一樣,野口鐵郞的研究乃是以白蓮敎為線索的。日本的明淸秘密宗敎硏究大多也是這個進路。但正因爲以白蓮敎爲線索,所以很自然地便將一般秘密宗敎類同於宣稱「天下大亂,彌勒下生」的白蓮敎宗敎性質。然而,正如李世瑜所說:「白蓮敎,明淸兩代也只是在官書、奏摺以及某些著述中做爲民間秘密宗敎的代稱,而各敎派本身則沒有自稱爲白蓮敎的」(《民間秘密宗敎史發凡•世界宗敎硏究》一九八九•一期)。即使從前的統治者把這些敎派含糊籠統一鍋粥地稱爲白蓮敎,我們做歷史研究宗敎研究的人,難道也可以如此嗎?明淸各種秘密宗敎,十分複雜,豈是一個彌勒信仰、一個白蓮造反的淵源,便能解釋的?例如羅敎,其《正敎除疑無修證自在寶卷》第十八品批評白蓮敎之拜月、燒紙、照水法等;第十九品又評破彌勒敎、玄鼓敎。當時人或許會說這只是掩飾面目之詞。現在來看,則羅敎與白蓮敎的不同,無論敎義與敎相,應該都是十分明顯的。又如黃天道,其敎義宗旨及修持內容,雖亦參用佛家名相,卻是以道敎內丹法爲主,與彌勒信仰的關係更淡。而且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兆惠的奏摺曾說:「普明一脈,實爲諸案邪敎之總」(見《軍機處附錄奏摺》。普明即黃天道敎主李賓的法號),則我們若換個角度,以黃天道爲明淸諸邪敎的主線來觀察,似乎也沒什麼不可以。倘或如此,其政敎關係恐伯就會與以白蓮爲主線者不同。因爲黃天道並不如白蓮敎那樣,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下生」,反而是要報皇恩、頌太平的(見馬西沙〈黃天敎源流考〉•世界宗敎硏究•一九八五•二期)。
因此,只以彌勒信仰來看明淸諸「邪敎」所引發的政敎衝突,是不夠的。白蓮敎的彌勒下生說,是否可以視爲各邪敎的共同特色,我頗爲懷疑。而且我們更應追問:許多敎派並無彌勒下生之說、並不反政權,爲何仍被視爲邪敎?又、佛敎本身即廣泛傳信彌勒淨土信仰,爲什麼淨土是正敎而白蓮敎便是邪敎?還有,如果僅從國家權力秩序這一面來看,邪敎之所以被目爲邪,是因爲它們冒犯了或否定了現世王權;正敎之所以爲正,則是由於它們甘於從屬王朝秩序。那麼,何以許多宗敎結社努力與官府妥協;它們宣傳的倫理道德,也普遍吸收了儒家禮法規範,卻不能改善其處境,仍然被判定爲邪敎?
您的評論: 注意: 評論內容不支持HTML代碼!
顧客評分: 差評 好評
請在下框輸入驗證號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