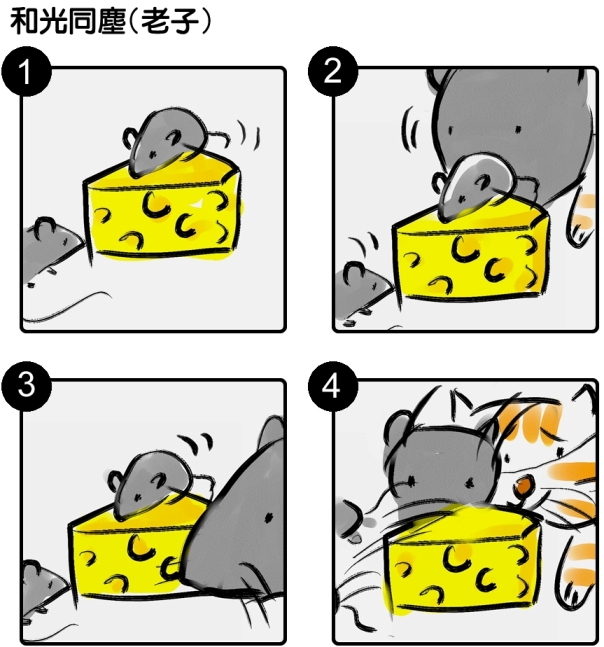莊子的生存哲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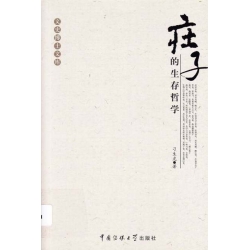 |
|
序
蔣凡
莊學,這是一個既誘人又神秘的學術領域,它既是哲學的,所以必須具有合乎理性的邏輯思維;同時,它又是藝術的美學的,所以又必須超越理性世界,作自由馳騁想像的直覺體悟。這是兩種很不相同的思維方式,看似矛盾相悖,彼此排拒,但其實又是相反相成,互相依存。在莊學研究中,二者如影之隨形,誰也離不開誰。這是由老莊之“道”的特殊本質所決定的。刁生虎博士正是根據自己長期潛心於莊子之“道”的研究與體悟,以實事求是的歷史精神和科學態度,把讀者引入到莊子世界的另一片新天地中。我有幸作為第一個讀者,讀其大著《莊子的生存哲學》後,感到非常受用而啟益良多,故略談體會以代序。
刁生虎博士治學,不僅重視古代文史的基礎功夫,而且富有理性思辨的睿智之光,艱難的思辨哲學問題,經他娓娓道來,化艱深為平易,令人眼睛豁然開朗。在莊學研究這個熱門課題中,他是別開生面,找到了莊子生存哲學這一個新鮮而巧妙的切入點。凡是人都要直面人生,所以討論生存問題就具有普遍意義。在其大著中,刁君如實地揭示了莊子生存哲學的奧秘,正好觸動了人類的一根最為敏感的神經。其學術視野新穎而開闊,在古今縱向的歷史比較及中西橫向的地域文化比較研究中,在生命困境中尋覓人生的超越之路。所論有九人方面,即人生論、生死論、語言論、天人論、宇宙論、物化論、科技論、生態論、思維論共九章,其新見紛呈而見其隻眼卓識,令人如行山陰道中而有目不暇接的美不勝收之感。
比如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中,到底是人定勝天,還是天人和諧呢?二者之爭,古今紛紜。在先秦時期,莊子認為“天與人不相勝”(《莊子•大宗師》),人不是自然的主人,而是自然的一分子,因而人不可以隨便破壞自然,而應採取人與“天”(即自然)和諧的態度,“順之以天理,應之以自然”(《莊子•天運》)。這在當時是一種新的思想觀念。而稍後於莊子的荀子則反之,他直截了當地批評說:“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他提出了以人類為主人為中的思想,明確指出:“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認為人是萬物之靈,人是自然的當然主人,應該驅遣自然來為人類服務。受其思想影響,後來就產生了人定勝天的堅定信念。這一理論曾指導了人類的科技活動和文明發展,在一定歷史階段推動了社會的發展,但時至今日,在科技與經濟發展的今天,卻又受到了非議。如美國的傑瑞米•裡夫金和特德•霍華德合著的《熵:一種新的世界觀》(呂明、袁周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就強烈批判了人定勝天之論,為拯救人類而勇敢地提出了理論挑戰。那麼究竟是天人和諧好呢,還是人定勝天正確呢?二者孰是孰非?我想,在特定的歷史階段,恐怕是各有其功過是非,難以一言以蔽之。在昔日特別是近現代的傳統思想研究中,大多是荀而非莊,學術界一般認為,荀論是合乎科學的先進的唯物主義,因而對於人定勝天之論,一片叫好:而對莊子的順天理應自然的和諧之論,則斥之為消極頹廢或復古倒退的主觀唯心主義,因而一筆予以抹煞。這公道嗎?刁生虎君在總結人類文明發展歷史的基礎上,指出了在科技文明高度發展的今天,要警惕人類中心主義,所以要正確理解莊子超前意識的有益啟示,亡羊補牢,尚未為晚,要求重新擺正人與自然的關係。他說,莊_-y-的“‘與天為徒’、‘天與人不相勝’,意味著‘天’與‘人’的關係不是互相克服、互相否定,而是互相融通、互相滲透的關係,這就充分體現了天人之間的絕對和諧與一致”。的確,人與自然不應該是敵對的關係,而應該是母親與兒子的關係。人視大地母親為敵人,則老天會視人為寇仇,一旦人類逆天無道,老天爺就會發怒而予以嚴酷報復,人類能無懼乎?環境污染、生態失衡等等,早已嚴重警告了人類。就說工廠、汽車所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等廢氣,嚴重污染了空氣,人能不呼吸嗎?而且,大氣臭氧層因此而被撕開了大口子,一旦繼續擴大,人類中又有誰能倖免宇宙射線的傷害呢?為此,刁君大聲疾呼:“人類生存延續的最大威脅來自人類自身,只重視科技理性而忽略價值理性的社會是很危險的,科技理性的過度膨脹必然會給人類帶來難以想像的災難。而要避免這一悲劇的發生,就必須意在大力提倡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充分弘揚科學精神的同時。還要有人文關懷,要通過人文關懷來彌補和克服科學的盲點和局限。……只有調整好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關係,學會用人文文化來調控科技文化,才能避免人類被科技異化的厄運和遭受自然懲罰的悲劇,只有在總體上理智地發展與自然的平衡與和諧,人類才能最終拯救和完善自己,可持續發展戰略才能最終得以順利實施。”(見第四章《天人論》)所言振聾發聵,勿謂人微言輕,該猛醒了,地球上的萬物之靈!
再如語言是人類的基本生存方式之一,古人就曾經說過:“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春秋穀粱傳•僖公二十二年》)這就決定了語言之思乃是哲學與生俱來的內在問題,中西哲學莫不如此。而語言作為一種符號系統,其基本功能是指稱物件,因而語言就與客觀物件有密切的聯繫。語言又與人的思維密不可分,人類思維的意向性賦予語言符號以一定的意義.於是語言的背後承載了人的觀念。由此可得到兩個主要關係:語言與指稱物件的關係,語言與思維的關係。語言與指稱物件的關係在中國古代是以“名實之辯”的名義展開的,而語言與思維的關係,則涉及到“言意之辯”的問題。”名實之辯”討論的是在認知領域內“名”與“實”是否存在著一一對應的關係,它主要關注的是在日常應用時語言如何指稱物件。“言意乏辯”涉及的討論層次已不同於“名實之辯”,由於“意”涉及到心理的層面即意向性的問題,使得討論的中心已不再局限於認知的範圍而達到形而上的層面。故從廣義語言哲學的角度進行考察,先秦諸子對於語言的思考主要涉及“名”與“實”和“言”與“意”兩方面的問題。前者主要討論的是語言與形而下的“物”的關係問題,後者主要討論的則是語言與形而上的“道”的關係問題。就前者而言,道家的莊子認為“名”不過是“實”的從屬、陪從、象徵而已,所以他在首篇《逍遙遊》中就明確指出:“名者,實之賓也。”接著莊子又在次篇《齊物論》中說:“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也就是道路是人走出來的,事物的名稱是人賦予它的,進一步肯定了“實”的第一性。後來莊子在《天道》篇中又有一個形象的說法:“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其意大概為不論“名”之當否,“我”固不失為“我”。也就是說“名”與“實”並沒有必然聯繫,“名”並不就是事物本身,只不過是指稱事物的語言符號而已。因而無論給事物取一個什麼“名”,都不會改變事物的“實”。以上三條顯例都意在說明一點,那就是在莊子的名實關係論中,他是堅定的重“實”輕“名”論者。這就說明莊子本人對日常語言的存在價值心存疑慮。再就後者而言,莊子的思考更是既深入又系統。對這方面的內容,刁生虎博士借助當前語言哲學的最新研究成果進行了深入、系統而又縝密的論述。其基本邏輯是:現實世界中確實存在有“可說”與“不可說”兩個領域,即一部分是可以用語言描繪、傳輸的形下現象世界,另一部分是無法用語言描繪、傳輸的形上本體世界。而莊子的貢獻就在於其不僅發現了“不可說”即“道不可言”這一哲學話語困境,並進而探討了產生這一語言困境的三大內在根源即言說主體“成心”之存在,言說物件“道”之本性和言說媒介“言”之物件化。而更為重要的是,莊子還發現了哲學“說“不可說”即“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這一獨特的歷史使命,把哲學的沉思由“說什麼”即“可說”還是“不可說”而轉向了“怎麼說”即“思維的說”還是“詩意的說”;其方法和路徑便在於使哲學言說方式從“思維的說”即莊子所說的“俗言”轉向“詩意的說”即莊子所說的“至言”,從而使哲學話語一變理性邏輯、主客二分的物件化語言即概念語言而為直覺體悟、天人合一的非物件化語言即隱喻語言,從而克服“不可說”這一語言困境,完成其“說“不可說”的哲學使命。而隱喻作為一種獨特的言說方式,其本身既具有詩的特質又具有思的意蘊,這就決定了文學與哲學本身就是其兩大功能。莊子正是以隱喻為恰切手段,借助于文學的形象外衣,傳輸了思想的抽象內涵,並最終形成了莊子文本詩思融合的獨特品格以及以直覺體悟為必要手段的“得意忘言”之解讀模式。莊子“三言”的隱喻表達就決定了莊子本身既是偉大的哲學家又是傑出的文學家之雙重身份。(見第三章《語言論》)刁君的這一論述是比較系統深刻的。
最後再說幾句題外話。教學相長,這是客觀的教育規律。作為大學老師,在四十餘年的漫長教學及科研的生涯中,我一直牢記唐朝韓愈《師說》提到的話:“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每一名博士生進校,都經過了嚴格淘汰與選拔,他們在校時雖然名為學生,但一般都各有專業嗜好與特長。孔夫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學生們對於自己的學習與研究,已入“樂之”之境,其學術自覺已化為生命的一部分,因而他們的“術業有專攻”,常令老師羡慕。因此,在長期的教學中,我既是老師,同時又是一名特殊的學生。現在雖已退休,但每一位學生的音容笑貌及其言語問答,至今仍歷歷在目而記憶猶新。從學生那兒我受到了許多啟發,從而在學術道路上盡了自己的綿薄之力,其間,我的許多著作,可說是師生交流的自然結晶.老師與學生,其名稱與位置是相對的,實際上,師生關係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體有盡,精神長存,只要薪盡火傳,自能發揚光大而期於不朽。我一生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學生大大超越諸位師長,在各自的領域中作出自己的獨特貢獻。學生的成就,就是老師的驕傲。奮發騰飛吧,每一位思念中的學生!
二零零七年春節後九日
於海上望珠樓半萬齋
您的評論: 注意: 評論內容不支持HTML代碼!
顧客評分: 差評 好評
請在下框輸入驗證號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