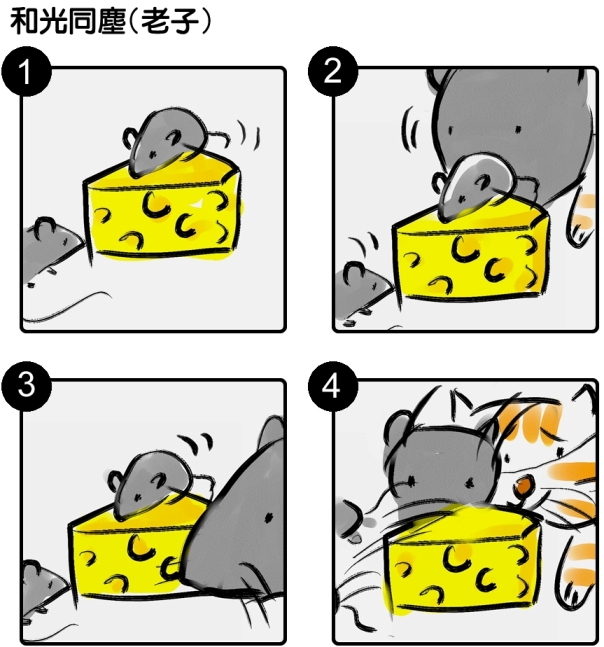莊子譯注
 |
|
序 言
縱觀中華民族的歷史,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波瀾壯闊、大變革的時代,也是一個百家爭鳴、人才輩出的時代。在這個百家爭鳴、人才輩出的時代中,諸子異峰突起,各俱崢嶸,而萬古風流。其中,便有一個稱之為“莊子”的人。他以其思想的博大精深,文章的洸洋自恣和人格的高潔脫俗著稱於世。而人們對他的認識,主要還是源于尚倖存傳世,以其姓為名的《莊子》一書。關於他的生平事蹟,流傳至今的史料不多,這是中國歷史的缺憾。
據[漢]司馬遷的《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雲:“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吋,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莊子,姓莊,名周,宋國蒙(今河南商丘縣東北)人。由他“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經馬敘倫考定,認為其生卒大約是西元前369年至前286年。他曾做過蒙地的漆園吏,後居於窮閭阨巷之中,以織屨為生。他鄙視以巧取豪奪、假仁實虐為業的帝王、諸侯和顯貴。楚威王曾遣使以重金聘其為相而不受。
關於他的著述,[漢]司馬遷的《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則雲:“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余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膚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在《史記》中,只提到其著作的部分篇名,據《漢書•藝文志》記載,《莊子》有五十二篇。但現存之《莊子》僅有三十三篇。現存《莊子》,很可能只是一個因名於“莊子”的莊子及其後學所作的殘存雜集而已,並非是莊子本人著作的全集或選集。因此,其難免魚龍混雜。
《莊子•天下》則稱曰:“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乙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穀。’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之博大真人哉!”
這是他對關尹、老聃之學的敬贊,也是對自己學說的肯定。
又稱曰:“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瑰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淑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于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于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這是他的自謙之辭,也是對自己學說之概括。
莊子所生活的時代,是一個史稱“春秋戰國”的諸侯爭雄、天下大亂的時代,也是一個史稱“百家爭鳴”的學術活躍、著書立說的時代。莊子便是這個時代學術界中的一個傑出代表。莊子博學眾采、精通家,見地深遠,在老子學說的基礎上形成了他自己獨特的思想體系和行文風格。
莊子思想的特點,是其自然道德觀,及以其對不公社會的批判,對自由人生的追求和對至德之世的嚮往。因此,其批判淋漓而盡致,其追求真執而樸實,其嚮往深沉而久遠。
他的自然道德觀,是其思想的基石。他說:“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複化為神奇,神奇複化為臭腐。故日:‘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北遊》)只有以此,才能洞觀莊子思想之奧妙。
他的社會批判之利劍,直指統治階級的總代表君王和其意識形態的“仁義”儒學。他抨擊道:“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徐無鬼》),“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同上)“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同上)“既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則陽》)
“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騙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遊。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散亂,吾惡能知其辯!”(《齊物論》)
“儒以詩禮發塚”(《外物》),“論則賤之,行則下之。”(《盜蹠》)“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同上)“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膚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同上)“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同上)指出:“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蹠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同上)
他控訴統治階級的貪婪暴虐和“聖賢”的“仁義禮教”把整個天下糟蹋得:“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人間世》)“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山木》)
他進一步推測和預言說:“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庚桑楚》)因此,他大聲疾呼:“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逍遙遊》)“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馬蹄》)“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胠篋》)
莊子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大動盪、大變革的時代,“美好”的公社制自然經濟早已逝去,殘酷的人人相欺的新社會已經到來,物質“文明”在飛速發展,歷史在大踏步前進。展示在他面前的,一方面是饑餓、苦難、死亡;另一方面是厭飽、淫樂、殺戮。極少數人的享樂、腐化建立在對絕大多數人的壓迫和剝削上,罪惡和苦難怵目驚心!極少數人為什麼能夠這樣做,而絕大多數人為什麼又能容忍其這樣做?人類被自己所創造的財富、文化和權力,即“物”,所統治和蹂躪。面對著這個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齊物論》),“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讓王》),人欲橫流的悲慘世界,他呼喚人類的覺醒,而告誡人們:“物物而不物於物”(《山木》),不要做“囿於物者”(《徐無鬼》),“不<要)以物易己”(同上),“不(要)以物易其性”(《駢拇》),“不(要)以物挫志”(《天地》),“不(要)以物害己”(《秋水》);警告統治者:“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在宥》)“不(要)以所用養害所養。”(《讓王》)“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在宥》),“無閉其情,物固自生”(同上);要求人類恢復其質樸之本性:“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閑,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刻意》)“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馬蹄》)“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外物》)他認為回到自然,才是人性的恢復和解放。這可能是世界思想史上最早有記載的“反異化”、“回歸自然”的呼聲,它的產生還在人類“文明”的發軔期,這似乎有點“太早”了,而為時人難以理解,認為這是瘋話,是癡人說夢。但這卻也正體現了他的天才和偉大。
他所追求的,是一種“無所待”而“逍遙”的自由人生。他說:“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核溺于馮氣,若負重行而上阪,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盜蹠》)“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山木》)“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藝概•卷二•詩概》)“莊子寓真於誕,寓實于玄,於此見寓言之妙。”(《藝概•卷一•文概》)
[民國]魯迅則評《莊子》曰:“汪洋辟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之。”(《漢文學史綱要》)
古之帝王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帝王、將相們的文治武功和富貴暴虐早已隨著如水的時光,煙消雲散了,但莊子之英名和宏論卻伴日月月而傳流不息。
莊子曰:“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漁父》)
演員在舞臺上的表演,無疑是他對劇本的一種再創造。演員沒有生活,不深入角色,就不能再現生活,而塑造出高於生活、感人肺腑的藝術典型。筆者在一個偶然機會中接觸到《莊子》;在對其流覽中,因感情受到其震撼,從而認真地研讀了它;由此,又產生把它介紹給世人而與之共用的打算;經數年之努力,今總算拙著草成。使今人難於理解《莊子》的原因,不僅在於古今文字和語意的天壌之別,主要還有個認識問題。甚至在當時,對莊子著述真正認識者,也寥若晨星。只有超越它,才可能認識它。因此,此書只是筆者個人對《莊子》體味的“充一”之言。其中錯誤、不當之處在所難免,請讀者批評指正。
“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是我們對待一切文學作品的通則。至於全面論述《莊子》,不是此書的任務,要知《莊子》之滋味,最好還是請讀者自己去品嘗它,那必定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但願此書對您閱讀《莊子》能有所幫助。
筆者
1995.5.5
您的評論: 注意: 評論內容不支持HTML代碼!
顧客評分: 差評 好評
請在下框輸入驗證號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