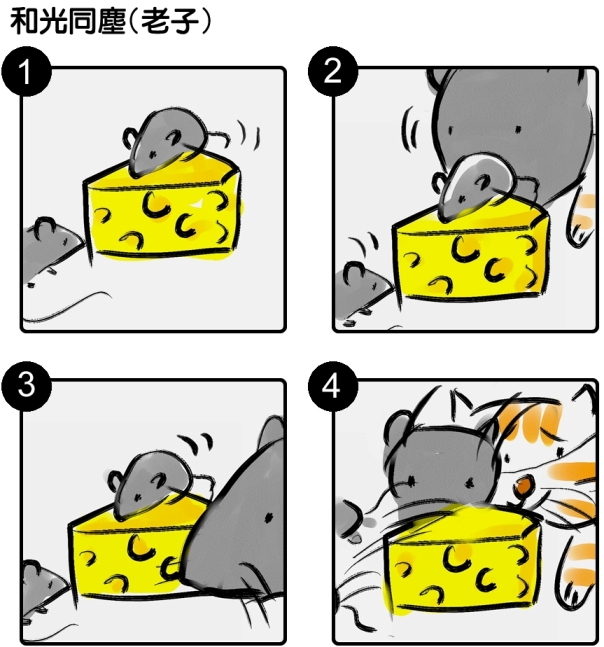王弼《老子注》研究
 |
|
序言:序“海外中國研究叢書”
中國曾經遺忘過世界,但世界卻並未因此而遺忘中國。令人嗟訝的是,20世紀60年代以後,就在中國越來越閉鎖的同時,世界各國的中國研究卻得到了越來越富於成果的發展。而到了中國門戶重開的今天,這種發展就把國內學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們不僅必須放眼海外去認識世界,還必須放眼海外來重新認識中國;不僅必須向國內讀者迻譯海外的西學,還必須向他們系統地介紹海外的中學。
這套書不可避免地會加深我們150年以來一直懷有的危機感和失落感,因為單是它的學術水準也足以提醒我們,中國文明在現時代所面對的絕不再是某個粗蠻不文的、很快就將被自己同化的、馬背上的戰勝者,而是一個高度發展了的、必將對自己的根本價值取向大大觸動的文明。可正因為這樣,借別人的眼光去獲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緊迫歷史使命,因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過強烈的反差反觀自身,中華文明就找不到進入其現代形態的入口。
當然,既是本著這樣的目的,我們就不能只從各家學說中篩選那些我們可以或者樂於接受的東西,否則我們的“篩子”本身就可能使讀者失去選擇、挑剔和批判的廣闊天地。我們的譯介畢竟還只是初步的嘗試,而我們所努力去做的,畢竟也只是和讀者一起去反復思索這些奉獻給大家的東西。
劉東
1988年秋於北京西八間房
譯者的話
人文研究的詮釋學性格意味著:思想和學術的創造幾乎總是在特定的詮釋學境域中展開的。在中國古代的學術和思想中,這一點尤為突出。上個世紀體系化地重構中國哲學史的努力,使得王弼思想的詮釋學基調被從整體上忽視了。在這樣的氛圍下,王弼《老子注》不是首先被當做注釋,而是被當做王弼本人的哲學構造來研究和引用的。王弼本人則被當成了某一類不受文本約束的“自由”的解釋者。
瓦格納(Rudolf G.Wagner)教授的《王弼(老子注)研究》在這樣的整體氛圍當中是一個輝煌的例外。作者首先致力於揭示王弼的注釋技藝。他向讀者呈現出了這樣一個王弼的形象:在自覺地接受文本的內在約束的前提下,在致力於消除文本的多義性的同時,將《老子》本文中所蘊涵的哲學可能性發闡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進而,作者將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既艱辛又充滿“危險”的工作當中:重構王弼的《老子》本和《老子注》,並給出結構性的轉寫和翻譯。在翻譯《老子》本文和王弼的注釋時,作者插入了大量推論性的成分,以盡可能地降低文本的多義性。與那種語焉不詳的翻譯相比,這樣的做法至少提供了一種可以“證偽”的譯本。而減少多義性這一根本指向,則充分體現了王弼《老子注》的基本精神。在上述文本研究的基礎上,作者對王弼政治哲學、語言哲學以及本體論的考察,向我們完整地展現了哲學素養和品味對於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毫不誇張地說,瓦格納教授的這部著怍在強調文本研究的思想史傳統中,是具有典範意義的。
中文版序
中國學研究發生在一個多語言的世界。除了中文以外,學者們還在用日語、英語、法語、德語以及其他語言撰寫重要的著作;而相當的歷史資料則在另一寬泛的語言跨度裏傳佈,從梵文到吐火羅文,從拉丁文到葡萄牙文,更不用說日文和韓文中對古漢語的運用了。幾乎沒有學者敢於聲稱自己在用所有這些語言中的哪怕一小半來從事研究,而與此同時,這樣的學術原則卻依然有效:關於一個課題的所有重要的資料和研究均需要順及,不管它們傳佈在哪種語言中。
在過去的25年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學研究在中國大陸經歷了實質性的復興,在海外出版的以及以其他語言撰寫的學術著作得到了應有的重視。某些影響廣泛的著作得到了譯介,以便於致力於中國學研究的學生和其他領域中那些關注比較視野的學者閱讀,比如裘錫圭的《文字學概要》。然而,這中間仍然存在著令人痛心的不對稱。當以漢語、英語、日語和法語等三或四種語言從事研究在海外中同學研究者中已經相當普及之時,在中國大陸,即使對於年輕一代學者,這也仍屬罕見。其結果是,他們的大多數討論被割離於國際學術的主流之外,這一事實受到了圖書館采選政策的強化——甚至在中國大陸最好的大學的圖書館裏,人們也能發現那些最重要的中國學研究的外文刊物付之闕如。
將外國的學術著作譯為漢語,至少能部分地彌補這一狀況。我很高興我關於王弼《老子注》的研究受到了關注,並被翻譯為中文出版。作為“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主編,劉東教授不僅是翻譯此書的建議者,而且也是此項翻譯計畫的每一步驟的積極推動者。我無法想像沒有他的努力,此書的翻譯能夠完成。
翻譯是真正多語際的工作。一個以德語為母語的學者,用中國學研究中應用最廣泛的學術語言——英語,分析和翻譯一部以3世紀的漢語寫成的,從語法、修辭和字義等方面解釋某個六百年前的文本的注釋。這一三卷本的研究包括對王弼在其注釋中所用的解釋學方法的分析,王弼《老子》本及往釋的批判性版本及“推論性翻譯”(即通過王弼的注釋解讀《老子》的文本),以及對作為王弼《老子注》核心的哲學問題的分析。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楊立華教授慨然承擔了這一譯介工作。為了形成一個翻譯規範,我們兩人有近兩個月的時間,每天在柏林的國際科學中心逐字校閱部分譯文,剩下的部分則通過信件交流和討論。這相當有趣,但也非常艱難——儘管楊立華的譯文草稿已經有了相當高的水準。
20世紀60年代初,我在德國和法圍學習期問,我關注的是古代漢語。那個時候很多研究古希臘的學者在學習占典的希臘文,但連在現代希臘的雅典餐館叫來一杯水這樣的事情也壓根兒無法做到。我那時既沒有學習現代的白話文,也沒有看到這樣做有什麼必要。那時候,社會主義陣營外的世界,與中國大陸沒有任何實質的學術交流,而少數在臺灣從事中國學研究的學者講的都是英語。直到1979年,我年近40的時候,我才學會了第一個普通話的單詞。對於充分發展我用現代漢語表達和寫作的能力來說,這實在太遲了。當然,我知道我的每一句話在說什麼,也能看出譯文是否準確地翻譯出了我的意圖,而楊立華則不得不一次次給出一個可用的現代漢語辭彙或句子。我非常感謝他容忍我無休止的細碎“嘮叨”的耐心。至於結果,則留待讀者的裁決。
這一研究並非憑空而來。它在與中國學研究領域中的學術傾向和實踐進行著或明或暗的爭辯。在現代的海外中國學研究開始的時候,人們可以期待它們會從歐洲古希臘和羅馬的經典研究的那些給人深刻印象的文本批判或文字學的方法論中汲取方法論的指引。在相鄰的領域——梵語研究中,情況正是如此。然而,西方學者在中國發現了有眾多學者參與其中的清代考據學傳統,其中的許多領域(如音韻學),達到了極為精深的水準。這一中國學的傳統迅速吸收了某些西方的文本批判方法,尤其是與辨偽問題相關的那些。其中最為突出的例子就是顧頡剛等人編輯的七卷本《古史辨》。而其他一些重要的西方文字學的要素,如批判性文本,則沒有成為中國學學術實踐的部分。除極少數例外,日本或西方的外國學者並沒有進入這一在質、量和歷史等方面都擁有如此優勢的領域的意圖。這一可悲的結果,致使時至今日,甚至那些最為基本的中國經典文本也沒有值得信賴的批判性版本。連可以和Oxford、Teubner或Loeb的西方經典著作系列相匹敵的東西都沒有,就更不用說有關《舊約》、《新約》的研究了。
帶有王弼注的《老子》本的通行本就是一個例證。它直接回到了帶有印在王弼注之上的《老子》文本的一個明代單行本,而這一《老子》文本顯然不是王弼手中的本子,因為王弼在注釋中引用的《老子》本文一再偏離它。而且,這一文本已經被廣泛地用作“王弼《老子》本”,甚至在那些將不同抄本並置起來的版本中也是如此。這一狀況在許多年前已經在實質上被島邦男教授的傑作改變了。他的《老子校正》是最早為《老子》傳承的不同世系建立批判性版本的。在他的著作之後發表的抄本,如馬王堆帛書本,在許多例證中證實了他對這些文本族中的兩個文本族的讀法。對馬王堆帛書本的盲目追隨,使得他的著作被絕大多數學者當做過時的東西而忽視。島邦男也是第一個將注釋中的引文用作這些注釋者手中的《老子》文本的資料的人。通過從他的著作中汲取重要的方法論明示並將其推展為更系統的方法,我開始著手建構王弼手中的《老子》本和王弼注釋本身的批判性版本,對於後者,明以前的資料尚存,而且在品質上也要好些。
我自己的方法論背景內在於解釋學傳統。1961年讀了伽達默爾(Gadamer)的《真理與方法》以後,為了學到更多的解釋學方法,我決定前往他當時任教的海德堡大學。儘管我盡力帶入這一視角來豐富我自己對中國學的研究和教學,我還是沒能說服伽達默爾把中國哲學作為哲學課程的常規部分。如果沒有在海德堡那些年的刺激,對王弼用於其注釋中、並使他的注釋為原本不同意其哲學宗旨和分析的學者信服的複雜方法和程式的分析,是無法想像的。這些分析構成了原本三卷系列的第一卷,亦即本書的第一編。這一分析的出現,包含了對忽視中國學研究中的注釋傳統的含蓄批評。一直以來,注釋者常常被學者們當做方便的參考書,用來檢索某個東西的意義,某個地方的古地名和位置以及某個漢字的罕見語義。如果注釋者被納入思想史或哲學史,他們就會被分配到這個或那個學派;他們的著作將被當做獨立的哲學論文,而幾乎完全忽略了這一事實:它們是作為另一有更高權威的文本的注釋來展開其論辯的。其結果是,它們與本文的互動關係、它們的注釋策略並沒有得到研究。這一部分力圖呈示這些策略及其暗示的研究的實質性哲學旨趣和一般性思想趣味。其中的一個結果是上面提到過的對文本的現代翻譯的深層策略。針對某種頗為時興的假設(它假設《老子》和王弼注都具有多種可能的意義,讀者可以自由發揮),我指出:王弼注的訴求是去除《老子》本文的所有可能的多義性。在王弼提供某種“翻譯”或以3世紀的語言詳盡闡發本文的內容和語法功能的地方,這一對多義性的去除是相當明確的。但在文本本身只有唯——種合理選項的場合下,仍然存在著含蓄性。如果在某個句子中,不知名的主角的行動對“百姓”具有普遍的影響,那麼,這意味著這個不知名的主角是統治者或整個政府,而非尊敬的讀者或我本人。對於現代的讀者,這些暗示不再是自明的了。因此,我把它們補充進括弧裏。其結果是,帶有明確性和可證偽性這兩種相互關聯的品質的一種現代漢語翻譯。對於學術探討而言,這樣做帶來的優點是:把我的翻譯開放給任何尖銳的批評性閱讀,容許發現和校正錯誤,而非隱藏在文本假定的多義性背後。
關於哲學的第三部分承擔了也許不可避免、但也令人遺憾的部分工作。例如,致力於研究新發現的竹簡或帛書抄本上的文字的學者,傾向於關注這一方面,而只對文本的修辭、敍事結構或它的政冶、哲學意涵做極少量的評注。很明顯,此種專門化是有其理由的,而且他們指派給技巧和純形式解決的特權位置避免了讓某個人對內容的解讀呈報出文本中的某個字得以辨識的方式的危險。與此同時,書寫符號與修辭和內容的分離,是純然表面性的。我的夢想是涵蓋從文本的版本到翮譯、從注釋策略的分析到哲學和政治意涵的研究的整個過程。我試圖保持三個部分的特質,並把他們設計在一種使之獨立停下的方式中。我也試圖整合它們。依據玄學家中的文字學和哲學實踐,我相信它是王弼力圖將文字學與哲學的迫切性結合起來的關鍵點。
研究王弼,整整用去了我23年的時間,這與他活過的年頭正好相當。不過,我要高興地說,我對此沒有絲毫遺憾。我非常期待看到中文讀者對我就這一年輕而驕傲的天才所做分析的反應。
2006年6月5日
於海德堡
書簡介
本書由三本主題互涉的獨立著作合併而成,內容涵蓋了對王弼《老子注》的解釋學方法的分析、王弼《老子》本及注釋的批判性版本及“推論性”翻譯(即符合王弼《老子》本解讀的翻譯),以及對作為王弼《老子注》核心的哲學問題的分析。通過審慎地重構王弼的《老子》本及《老子注》,本書找到了探討王弼的注釋技藝的堅實基礎。在將王弼《老子注》置入與其他競爭性注釋並存的語境,並抽繹出這些競爭性注釋的解讀策略的過程中,本書向讀者清晰地呈示出理解《老子》的眾多路徑:從根本性的哲學創作、特定的政治理論到長生術的指南,以及在如此眾多的路徑中王弼的哲學取徑所達到的高度。
您的評論: 注意: 評論內容不支持HTML代碼!
顧客評分: 差評 好評
請在下框輸入驗證號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