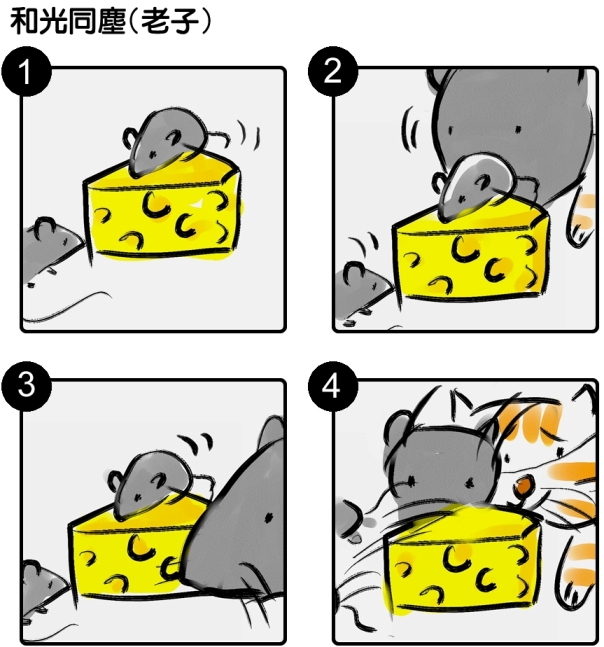《文子》成書及其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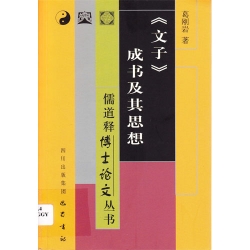 |
|
《文子》一書,二十多年以前在道教經典中和在先秦諸子中的地位,可以說一在九天之上,一在九地之下。至1973年定州西漢墓出土了《文子》殘本,它作為思想史的著作才得到人們的重視。《文子》從魏晉時代起,一直受到道教學者的重視。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置崇玄學,規定“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新唐書·選舉志》),其學問成了選拔人才的科目。天寶元年詔封文子為通玄真人,改《文子》為《通玄真經》,名列《道德真經》、《南華真經》之後,為道教的第三大經典,因而此後出現了不少注本。但是在道教之外,《文子》一書幾乎沒有任何地位。這同班固在《漢書·藝文志》的《文子》書目下注的“似依託者也”一句話不無關係,但也同今本《文子》一書的複雜情況有關。以往學者們一方面由於見到的資料有限,一方面由於思想方法方面的原因,對《文子》一書一些問題的處理顯然是簡單化了。
論及《文子》,不可避免地先要說到文子其人,事實上人們在對《文子》一書真偽的判斷中,也都無形中將二者聯繫起來看。《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類“《文子》九篇”下,班固自注:
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在很多人看來,如《文子》是文子所著,文子又是老子弟子,或是周平王時人,便可認為其書是“真”:如《文子》雖先秦時書,但非文子所著,則是“依託”,而過去等同於偽:如作者雖先秦時人但或非老子弟子,或非周平王時人,也算依託。所以,我們在論《文子》此書之前,先說說文子其人。
《文子》書中提到的“平王”,其前並無“周”字。班固注說是“稱周平王問”,則他理解書中“平王”為周平王。按理,如周平王時無文子其人,則不可能有依託周平王之事,所以班固於《漢書·古今人表》的“中中”秦襄公之後列有“文子”,時代大體與周平王相應。不過班固也認為這個文子未必同《文子》一書有什麼關係;他認為同《文子》一書有關的人為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所以他說:“似依託者也。”學者們未能深思,以為班固在《漢書》中的表述自相矛盾。其實班固在沒有更充分證據的情況下,採用了疑以傳疑的辦法,態度是謹慎的。
儘管大部分人誤解班固的話,以人及書,多以《文子》為偽書,但也有些學者對此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討。馬瑞臨《文獻通考》引《周氏涉筆》雲:“其稱平王者,往往是楚平王。序者以周平王時人,非也。”楚平王(前528—前516年在位)同老子(前580—前500年)大體同時,而較孔子(前551—前479年)稍早,如以文子為老子弟子中年紀大者,則其說也不是沒有成立之可能。故孫星衍便主張此說。孫星衍《文子序》一文就《漢書·藝文志》中的班固注做瞭解釋:“蓋謂文子生不與周平王同時,而書中稱之,乃托為問答,非謂其書由後人偽託。宋人誤會其言,遂疑此書出於後世也。”又雲:“書稱平王,並無‘周’字,班固誤讀此書。此平王何知非楚平王?”上引前數語是解釋班固注並說明後人對班固注的誤解,完全正確。上引後數語是對班固以《文子》一書中的“平王”為“周平王”提出看法。自1973年河北省定州八角廊出土了《文子》殘簡,不少學者傾向於這個看法,以為書中平王為楚平王。但也有學者據蒙文通先生之說,以為《文子》中表現的是北方道家思想,不同于楚國流行的南方道家思想,文子應為北方學者,不當在楚,不同意“楚平王”之說。我以為蒙文通先生所言是戰國中期以後的情況,戰國中期莊周一派更加突出了老子對社會和統治階級文化的批判,否定仁義,而北方的道家則有不少地方同儒家思想表現出一定的
一致性,但春秋戰國之間尚無此種分化。今本《老子》第十九章的“絕仁棄義”,郭店楚簡本作“絕偽棄慮”,就說明這一點。所以。以《文子》中“平王”為楚平王,同《漢書·藝文心志》言文子為“老子弟子”之說,也並不矛盾。這裏確實存在著探索文子其人的空間。
北魏李暹《文子注》解釋說:“姓辛氏,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範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三引)此說在時代上同“老子弟子”之說完全符合。但據錢穆考證,“計然”乃範蠡所著書名(意思為謀事之然者,也即謀行事成功之書)。錢氏列十事以證之,確鑿可信。這裏還可以補充一條證據:《國語·吳語》中言“越王勾踐乃召其五大夫”,以下大夫舌庸、大夫苦成、大夫種、大夫蠡、大夫皋如皆有進言,獨無所謂計然。學者們主計然為人名的最重要的證據是《史記·貨殖列傳》“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範蠡計然”一句。而從上面的事實看,“計然”顯然為書名。班固誤讀《史記》,以計然為人名,列於《古今人表》:《吳越春秋》也因而加以敷衍,其後韋昭、徐廣及《史記集解》、《史記索隱》陳陳相因,皆以計然為人名。若果真《史記》中“計然”為人名,越王勾踐召其大夫,首先應是計然,而事實上卻沒有。同時,《國語》、《左傳》中也不見“計然”之名,則“計然”本為書名,無可懷疑。李暹是依據了後人所編《範子》中的文字,其書在整理中摻雜進後來的材料,也常見之事。《範子》中的“葵丘濮上人”及“其先晉亡公子也”之語,也應是牽附了其他的人事。而李善竟信其說(《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注),孫星衍也以為“文子即計然無疑”,應該說是通人之蔽。
但所謂“範蠡之師”的說法也不是完全向壁虛造。我懷疑這個傳說的形成同文種有關。《國語·越語下》載範蠡對越王勾踐語:“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之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睦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這裏所談文種的思想特徵同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說的“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因時為業”、“因物與合”的道家思想頗為一致。《國語·越語上》又載文種諫越王的一段話,其中說:“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稀,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這同《論六家要旨》中說的“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的道家思想也一致。當夫差起師伐越之時越王勾踐將起兵迎戰,而文種言:“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也。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云云,勸越王先求行成,以柔弱下之,最後勝越,這也正是《老子》和簡本《文子》所主張的虛靜、柔後的思想。過去有的學者認為《老子》是一部兵書,早期道教並不是不言兵。所以,清人江瑔《讀子卮言》提出文子即文種之說。以文子為文種,時代上同“與孔子並時”之說相合,姓氏相投,思想上也比較接近。
當然也還有一個問題,即簡本《文子》中的兩次說到“天王”。這是我們認《文子》中的平王為周平王的證據。但吳王夫差也被越國使臣稱之為“天王”,而這使臣正是文種同越王合計之後,越王聽文種之言而派去的,如果說這使臣是受了文種的指教,亦無不可。陸機《豪士賦》雲:“文子懷忠敬而齒劍。”李善注引《史記》和《吳越春秋》文,以為即指文種,按之史事應該無誤。《抱朴子外篇·知止》“文子以九術霸越”,則“文子”指文種甚明。所以,我以為前人以《文子》作者為范蠡師,應是由文種誤傳而成。
以上只是要說明“《文子》中平王為楚平王”說,“文子即計然說”、“文子即文種說”之產生都有著文獻上、傳說上和有的人思想與《文子》相近等等的原因。我們研討古代文獻,應對古人抱著一個理解的態度,不要認為古代有很多人專門作偽,造作謊言。我這樣說並不等於稀泥抹光牆,不論正誤,不分是非。我只是說:只有抱著這種理解古人的態度才能對有些問題作出公正的客觀的判斷。比如“文子就是文種”說,由我上面所論可以看出,理由是比較充分的。但我覺得還是有問題。因為楚平王死的一年(前516年)下距吳亡(前473年)43年。吳亡之後勾踐尚不放心文種,令其自裁,則吳亡之時文種年歲不會超過六十五歲。那麼,楚平王卒之年,文種年歲不會超過二十二歲。這同書中平王恭敬請問的身份不符。故雖然《越絕書》卷六言文種在楚為大夫,《史記正義》引《吳越春秋》佚文言“大夫種姓文,字子禽,荊平王時為宛令”,但我還是以為《文子》一書所記乃文種在入越之前同楚平王的對話,差不多沒有可能;如真的是文種,則是入越之後借著同楚平王的對話,而寫出了自己的一些政治見解,並非紀實之言。
今人李定塵先生大約也是因為楚平王時代稍早之故,提出齊平公(前480—前456年在位)之說。王國維《古諸侯稱王說》列大量證據說明“古諸侯於境內稱王,與稱君稱公無異”。則齊平公在其境內可以稱王。唯齊平公之時薑齊政衰,田氏專權,“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在這樣的情況下,齊平公是否還有可能同有的文人從容討論有道無道、治國為政,談什麼“帝王之功成矣”(0929簡),論什麼“王若能得其道而勿廢,傳之後嗣”
(0892簡),“人民和陸(睦),長有其國”(2218簡)。李定生先生舉《韓非子·內儲說上》“齊王問于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 :‘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就其思想和反映出的身份來說,應同作為思想家的文子一致,而不符合田文(孟嘗君)的口吻,此文字非田文,可以肯定。但那齊王是否是齊平公,就難說。當然,這仍然可以作為繼續探索的一個線索。
又《史記·孟子苟卿列傳》司馬貞《索隱》引《別錄》雲:“今案《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即子夏之弟子,問于墨子。”但《文子》一書的思想即不同于子夏一派的注重《詩》、《書》典籍,也沒有墨家的思想特徵,同時今本《墨子》中並無“文子”其人。我以為《別錄》中這個“文子”乃是“禽子”字壞而誤(“禽”字當中含有“文”字,字殘損成“文”字)。墨子弟子禽滑又稱“禽子”,見《墨子·所染》。《史記·儒林列傳》“田子方,段幹木,吳起,禽滑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正與《別錄》佚文中所謂“文子”的情形相合。所以此條材料難以依據。
歸結起來,我以為歷史上的文子其人,是存在的,關於他的具體生平、身份等仍然需要從班固疑以傳疑所提供的兩條資訊中去找:一為“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二為周平王時代。
我猜想:文子應是周天子的同姓,以文為氏,因其疏遠,而以文史典籍為務。《通志·氏族四》:“文氏,姬姓。《風俗通》雲:‘文氏,周文王支孫,以諡為氏。越大夫文種。’”言文氏為文王之後,無線索可錄,未必可靠。但其為姬姓,應非虛造。晉為姬姓(武王子唐叔虞之後),故《範子》中言文子“其先晉亡公子也”,應非完全無據。那麼文子以同姓貴族的身份同周平王對話,是有可能的。
但話說回來,《文子》一書,卻肯定既非周平王時人所著,也非春秋戰國之間人所完成。因為簡本《文子》中反應出的關於“道”、“仁”、“仁義”等哲學與倫理方面的概念都是春秋末年才形成的。 事實上,《文子》一書形成的過程十分複雜。就原本《文子》而言,其中應包含有一些春秋戰國之間的材料,而主要為戰國晚期的東西。至魏晉之時由於長期戰亂,典籍散佚,而道教又得到大的發展,道教學者出於道教經典建設的目的,在道家著作《文子》殘本的基礎上抄錄《淮南子》等書加以補充,使之成為綜合了漢代以前南北道家思想的一部重要道教經典。從北魏末年(約當南朝的齊梁時代)至唐貞觀年間又進一步完成了形式上的改造和名稱的變化,成為所謂《通玄真經》。我以為作為諸子之作的《文子》應以簡本為主,參之以今本《文子》中除去與《淮南子》相重文字的部分;而作為道教的經典可以今本《文子》即《通玄真經》為主。不必因為前者而否定後者,也不必因為後者而貶低前者。
王利器先生的《文子疏義》已列入《新編諸子集成》之中。20世紀30年代世界書局出版的《諸子集成》將以前被判為偽書的《文子》、《尉繚子》、《六韜》、《鬼穀子》、《屍子》、《冠子》等排除在外。由近二三十年出土地下文獻看,這些書並非偽書。將它們列入《新編諸子集成》,可以擴大先秦諸子研究的範圍,增加中國哲學、政治、經濟、美學等研究的思想資源。遺憾的是王先生在杜道堅“《文子》,《道德》之疏義”之說的基礎上,提出“《淮南》,《文子》之疏義也”的觀點,不僅不區分簡本、今本的不同,也將從原本到今本很長時問中形成的種種複雜現象隱蔽起來。
李定生、徐慧君二位於1988年出版了《文子要詮》,很快銷售告罄,反映了學者們希望以科學的態度重新看待、研究這部書的企盼與迫切心情。2004年又出版了他們在前一書基礎上修訂完成的《文子校釋》,書前有在此前發表論文基礎上寫的《論文子》作為代前言,書末且附了《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正文中問對體篇章中的人稱,也據簡本《文子》作了校改。應該說這是《文子》研究上的一個很大的進步。李定生先生在文子其人其書的研究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提出了一些有價值或具有啟發性的看法,對今本《文子》的思想也作了深入的探討。但李定生先生同樣忽視了《文子》這部書從魏晉至初唐三百多年中在內容上所經歷的巨大變化,不分原本和今本,籠統地認為“《文子》是先於《淮南子》的先秦古籍”,將二書多所相同的現象歸結為“是《淮南子》抄襲《文子》”。
另外由於簡本《文子》的發現,也有對今本《文子》的價值忽視和貶低的傾向。我們認為今本《文子》是道教早期理論建設中的重要論著。原本《文子》的散佚是諸子書的一大損失,但從道教的方面來說,經過增補,吸納了《淮南子》的一些內容,大大地豐富和發展了《老子》一書的道論,所以成了地位僅次於《道德經》、《南華經》的重要經典。前些年見到某出版社出版的《道學十三經》,包括《道德真經》、《南華真經》、《沖虛真經》、《周易參同契》、《抱樸子內篇》、《老子想爾注》、《老子中經》、《黃庭經》、《太平經》、《玉皇經》、《黃帝陰符經》、《清淨經》、《悟真篇》。選至宋代,而不及《通玄真經》,令人不能理解。作為道教的元典,《通玄真經》是應該收入的。另外,《洞靈真經》(《庚桑子》)雖雜取《莊》、《列》、《老》、《文》、《商》及《呂氏春秋》、《說苑》、《新序》諸書,但頗有理致,亦不當廢。而從道教文化的方面說《老子中經》(《珠宮玉曆》)、《玉皇經》絕不能同它們相比。北京出版社1996年出版《道學精華》選道學重要著作28種,也沒有《文子》、《庚桑子》(又作《亢倉子》),同樣反映著認識上的偏頗。
有鑒於這些情況,我們認為《文子》這部書仍有必要再作深入細緻的探討。
葛剛岩同志在我處攻讀博士學位,他研讀了簡本《文子》和今本《文子》後,對這部書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鼓勵他就這個充滿了問題的課題作一努力,於是確定為他的學位論文選題。他不但對這個選題充滿了熱情,而且確實下了很大的功夫。自《文物》雜誌1995年12期公佈了定州出土的漢簡《文子》以來,不少學養深厚的學者都關注它,並發表了論文,各家都講得有道理,但總體上又存在很多矛盾。從對這部書的價值的重視方面說。我們同王利器先生、李定生先生等很多學界的朋友們是一樣的,我對葛剛岩同志說:“不要希望徹底地解決問題,只要認真地分析簡本、今本反映出的一些現象,實事求是,弄清一些基本事實,就是成績。”葛剛岩同志為這個課題幾個假期沒有回家,研讀有關文獻和十年來學者們的論著,他採取多學科結合的辦法,運用多種研究手段,常因此而廢寢忘食。經過兩年左右的努力,終於於2004年春完成了學位論文《文子成書及其思想》。論文對文子其人尤其是《文子》一書中一些爭論較大的問題上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在前修時賢的基礎上,宏觀把握,清理材料,擇善而從,合理推論,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這無論從思想史還是從宗教學的角度看,都是有意義的。
綜觀葛剛岩同志這部書,我覺得有這麼幾個特點:
第一,對前修時賢之說,都給以廣泛的關注並進行認真的研讀,但其依違去取,概以簡本《文子》和今本《文子》所反映出的事實為准。比如,究竟是《文子》抄了《淮南子》,還是《淮南子》抄了《文子》,這兩種看法都有些學問淵博、治學嚴謹、很有聲望的學者支持。王應麟言《文子》之言“其見於《列》、《莊》、《淮南》者不可縷數”(《困學紀聞》卷十);王念孫《讀書雜誌》舉三例以明《淮南子》誤讀《文子》原文,或易字,或增字,皆失其本義;孫星衍舉例以證《淮南子》“多引《文子》,增損其詞,謬誤迭出”(《問字堂集·文子序》)。今人王利器先生的煌煌大著《文子疏義》三十餘萬字,其目的即在“就《淮南》之括、衍繹《文子》為言者,句疏字櫛而比義之” (《文子疏義序》);李定生、徐慧君二位《文子校釋》之《代前言》又從幾個方面來論證《淮南子》抄《文子》之事實。而主張《文子》抄《淮南子》者自柳宗元《辯文子》提出“駁書”說之後,有不少人實證以論《文子》抄《淮南子》。清錢熙祚以《文子》與《淮南子》互校,言“乃知此書之誤,誤於作偽者半,誤於傳寫者亦半”。“《文子》出《淮南子》十之九,取它書十之一也”(《文子校勘記》。王重民《文子校記》、王叔岷《文子斟證》皆稱作顧觀光《劄記》,或顧觀光所代作)。章太炎也言“今之《文子》半襲《淮南》”(《菿漢三言》)。王叔岷《文子斟證》更是細心爬梳,以具體揭示《文子》是如何抄襲《淮南子》的。在這種情況下要作出一個判斷是困難的。葛剛岩同志將簡本《文子》與今本《文子》皆輸入電腦,對兩書相重的部分從詞語、句式、篇章變化、思想等各個方面逐句進行細緻的比較、分析。對其中一些問題我們也一起認真地討論過。
確實如有的學者所言,也有簡本《文子》中的文字錯而今本《文子》中正確,或簡本中失其義而今本的表達更能體現全書思想得地方。但全面來看,綜合分析,還是今本《文子》抄了《淮南子》,而不是相反。這在書中講得很充分,這裏不必舉例。對於簡本勝於今本的和今本勝於簡本的實例作具體分析,我們認為簡本中的個別錯誤是傳抄中形成的,因為簡本在埋入地下之前也已經經歷了較長一段時間;而文意和句式、用詞方面今本較簡本勝的地方,也有今本又經過後人潤飾、修改的因素在內,但今本《文子》中大段大段文字由《淮南子》刪並、集約而成的跡象則是不能反過來解釋的。當然,確定是今本《文子》抄了《淮南子》,還因為簡本《文子》竟沒有一點與《淮南子》相重的部分,這也不是以“偶然”二字可以解釋得了的。
從書中可以看出葛剛岩對於即使他並不贊成的觀點,也予以注意。書中的個別結論也可能只是一種推論或假設,但其中並無任何先人為主的地方。
據我所知,葛剛岩同志在一些問題的看法上也有過轉變,其原因也同樣是出於對《文子》文本理解、認識的加深以及對簡本,今本異同分析的深入。比如他開始時同意李定生先生的看法,認為春秋戰國之間有一個文子,但後來他放棄了這個看法,主要由於簡本中的“天王”問題在春秋戰國這一段中很難解決。
第二,這本書雖然側重於文獻學的研究,大量的精力用於對
一些具體材料的分析、對比和研究,但在很多問題的研究中總是考慮到春秋戰國至唐代這個漫長時期學術思想、文化發展的大勢。他在這段時間讀了任繼愈先生主編的《中國哲學發展史》、《中國道教史》,卿希泰先生主編的《中國道教史》等哲學史、道教史著作和有關文獻學方面的論著,也研讀了其他一些道學方面的論著。我認為,這樣可以避免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可以避免提出的看法局部說來很有道理,而整體上或放到大的時代背景中難以成立的情況。
《文子》是一部問題很多、歷來學者們看法分歧很大的著作,葛剛岩同志在當代很多學養深厚的學者之後,面對很多矛盾,不畏困難,認真鑽研,提出了一些看法,理清了一些問題,完成了這一部書,無論從哪個方面說都是有意義的。當然,書中的一些結論只是一家之言,也只是他目前階段的認識,還需要經過以後研究的檢驗。但把它發表出來引起大家的進一步的討論,總比個人孤立地摸索要好。該書經卿希泰先生閱正,川大宗教研究所和《儒道釋博士論文叢書》編輯委員會評審列入《儒道釋博士論文叢書》,即將出版,剛岩同志要我寫序,寫出以上感想,望各位同仁指正。
《儒道釋博士論文叢書》緣起
儒道釋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三大支柱,源遠流長,內容豐富,影響深遠,它對中華民族的共同心理、共同感情和強大凝聚力的形成與發展,均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是我們幾千年來戰勝一切困難、經過無數險阻、始終立於不敗之地的精神武器,在今人仍然顯示著它的強大生命力,並在新的世紀裏,煥發出更加燦爛的光彩。
自從197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路線以來,我國對儒道釋傳統文化的研究工作,也有了很大的發發展在全國各地設立了許多博士點,使年輕的研究人才的培養工作走上了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的軌道,一批又一批的博士畢業生正在茁壯成長,他們是我國傳統文化研究方面的一支強大的新生力量,是有關各學科未來的學術帶頭人。他們的博士學位論文有一部分在出版之後,已在國內外的同行學者中受到了關注,產生了很好的影響。但因種種原因,學術著作的出版甚難,尤其是中青年學者的學術著作出版更難。因此還有相當多的博士學位論文難以及時發表。不及時解決這一難題,不僅對中青年學者的成長不利,且對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促進學術交流也不利。我們有志於解決此一難題久矣,始終均以各種原因未能如願。近與香港圓玄學院商議,喜得該院慨然允諾捐資贊助出版《儒道釋博士論文叢書》,這將是學術界的一大盛事,長期堅持下去,必然會產生它的深遠影響。
本叢書面向全國(包括港澳臺地區)徵稿。凡是以研究儒、道、釋為內容的博士學位論文,皆屬本叢書的出版範圍,均可向本叢書的編委會提出出版申請。
本叢書的編委會是由各有關專家組成,負責審定申請者的博士學位論文的入選工作。我們掌握的入選條件是:(1)對有關學科帶前沿性的重大問題作出創造性研究的;(2)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新的重大突破、得出新的科學結論從而推動了本學科向前發展的;(3)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對學科建設具有較大貢獻的。凡具備其中的任何一條,均可入選。但我們對入選論文還有一個最基本的共同要求,這就是文章觀點的取得和論證,都須有科學的依據,應在充分佔有第一手原始資料的基礎上進行,並詳細注明這些資料的來源和出處,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避免誇誇其談,華而不實。我們提出這個最基本的共同要求,其目的乃是期望通過本叢書的出版工作,在年輕學者中宣導一種實事求是地、一步一個腳印地進行學術研究的嚴謹學風。 由於編委會學識水準有限和經驗與人力的不足,難免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失誤,懇切希望能夠得到全國各有關博士點和博士導師以及博士研究生們的大力支持和幫助,對我們的工作提出批評和建議,加強聯繫和合作,給我們推薦和投寄好的書稿,讓我們一道為搞好《儒道釋博-士-論文叢書》的出版工作、為繁榮祖國的學術文化事業而共同努力。
2005年8月5日於四川大學宗教與社會
您的評論: 注意: 評論內容不支持HTML代碼!
顧客評分: 差評 好評
請在下框輸入驗證號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