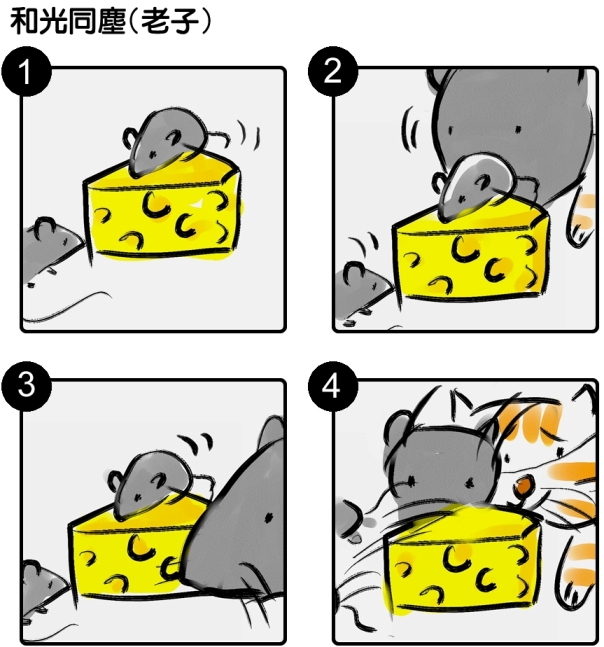中國思想地圖老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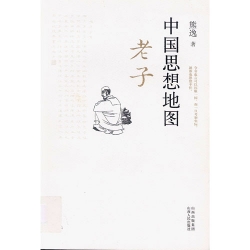 |
|
序言:
“中國思想地圖”這個系列,本意是把中國思想史上的要點、節點論述清楚,並逐漸把脈絡勾畫出來,通俗以陳說之。這本書是本系列的第一本,也不知道有沒有開出一個好頭。
這本書更多地把《老子》拉到形而下的層面上來作辨析,重點著眼於它在政治學和社會學上的意義。——並不是我特意選取了這個角度,而是我以為《老子》原本的關注焦點就是形而下的,這在書中會有相應的論述,連帶著對前人的一些導向形而上的成說也有相應的辨駁。
在這樣的視角確立之後,本書進而分析《老子》若干重點議題的來龍去脈,考察《老子》特殊的論證方式和理論的自洽性,站在前輩學者的肩膀上略有一已之得。力有未逮,謹供方家批判。
“道可道,非常道”。在進入正題之前,先要澄清一個流傳較廣的誤解。南懷瑾老先生講過:“有人解釋《老子》第一章首句的第二個‘道’字,便是一般所謂‘常言道’的意思,也就是說話的意思。其實,這是不大合理的。因為把說話或話說用‘道’字來代表,那是唐宋之間的口頭語。”(《老子他說》)
但事實是,唐宋以前“道”就有了“說”的意思,比如《史記.刺客列傳》,燕太子丹和鞠武商量著怎麼安置從秦國逃過來的樊於期將軍,鞠武就說:“且以雕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史記•李將軍列傳》,漢文帝很欣賞李廣的勇武,但感歎他生不逢時,說李廣如果生活在漢高帝劉邦的時代,“萬戶侯豈足道哉”。
更要緊的是,西漢前期的道家權威就已經用“說”來解釋這個“道”了;在先秦的典籍裏,“道”也已經有了“說”的意思,儘管並不多見。比如《荀子。非相》有“學者不道也”,《荀子•儒效》有“客有道曰……”,《詩經•鄘風•牆有茨》有“中苒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1]
————————
[1] 不止漢語有這種情況,錢鐘書先生言:古希臘文“道”(logos)兼“理”(ratio)與“言”(oratio),可以相參。(《管錐編》)這不知道是巧合還是有什麼深意。張隆溪先生認為這或許只是一種巧合,但這種巧合也點出了這個思與言的問題或辯證是東西方共有的,儘管表現為不同的形式。(Qian Zhongshu on Philo-sophical and Mystical Paradoxes in the Laozi)
所以,我這裏還是繼續依照傳統,把“道可道,非常道”理解作“可以用言語表達的道,就不是常‘道’”。
“道”,可道還是不可道,這是一個問題。形而下地說,正是這個問題把人群一分為二,相信“道可道”的是一種人,相信“道可道,非常道”的是另一種人。
前一種人偏於理性,喜歡探求知識,凡事講邏輯、講證據,如果想要他們相信你的話,你就需要提供給他們足夠的證據,由著他們去辨析、檢驗,直到確認無誤為止。而且他們也甘願承受許多沒有答案的問題,信者存信,疑者存疑。這種人接受新東西,靠的是一個字:“懂”。
後一種人卻不同,他們也許會鄙薄前一種人,認為那種人即便有時也會欣賞美色,但能夠欣賞的至多不過是那類“紅紅的臉、膀寬腰圓、骨骼粗大、肌肉豐滿的生理學上的美人”——這是二葉亭四迷在《浮雲》裏的一個絕佳形容。而他們自己,偏於感性,對邏輯和證據並不太在意,如果你想要他們相信你的話,任你給出再充足的證據、再嚴密的推理,也不會有多大作用,關鍵要看你的話能否打動他們。
他們的思考方式,用詩人波德賴爾的話說,就是“音樂式的和繪畫式的,不耍弄詭辯,不使用三段論,也不用演繹法”。但對於證實,“除非在我們的脈搏上得到證實,哲學上的定理也還不能算作定理”——這是濟慈的話,還是詩人的語言。
再有,他們通常也不大容易承受許多沒有答案的問題。他們需要斬釘截鐵的答案,而無論這樣的答案是否有著足夠的證據來作支撐。他們接受新東西,靠的是另一個字:“悟”。
所以,道,到底能不能被講清楚,這雖然也取決於講述者,但更加取決於聽眾。甚至對後一種人來說,不講清楚或者講不清楚才是最好的結果,畢竟人生總需要一點神神秘秘、高深莫測的東西,也只有這樣的東西才適合作為一個人的永恆的精神支柱。也許正是出於同樣的感受,伯特蘭.羅素在談論偉大的柏拉圖的時候,才會以這樣一句話作為開場白:“頌揚柏拉圖——但不是理解柏拉圖——總歸是正確的。這正是偉大人物們的共同命運。”
所以許多人願意相信(“願意相信”往往就直接和“相信”畫等號了),我們的一位名叫李耳的祖先已經在兩千多年前洞悉了天地間最核心的規律,並且用一種神秘的語言啟示世人,於是,無論是今天的中華民族將要在世界上崛起,還是張三、李四把自身昇華到一種至高無上的精神境界,都仰賴於對《老子》這部書的悉心感悟。
也就是說,《老子》這部書上可以洞徹天機,中可以安邦定國,下可以作為一個人的勵志枕邊書,指導任何時代的任何人如何修身養性,如何為人處事,甚至如何緩解失戀的痛苦,如何挨過失業的打擊。也許,當我們被黑心老闆無故克扣了大把工錢,正猶豫著要不要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的時候,“算了吧”,我們畢竟還可以這樣安慰自己,“唯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老子》這部書,如果要“悟”,可以悟得天花亂墜;但如果要“懂”,那就費力多了。
所謂費力,需要分兩個層面來說。在超驗的層面上,就像Liv-ia Kohn歸納的那樣:“道”之所以無法用語言表達,是因為語言屬於辨別力和知識領域的一部分,而“道”是超越它們的;語言是現實世界的一個產物,“道”則是超越現實世界的。“道”是先驗的、無所不在的,它創造、構建整個宇宙,並賦之以秩序,它並不是宇宙的一個部分。(The Taoist Experience:An Anthology)
話雖如此,但即便我們去看看道教那些玄而又玄的典籍,比如著名的《道體論》(大約出於唐代),文章是用問答的形式,提問的人在得到答案之後有時還不敢肯定,於是乎多問一句“你是怎麼知道的”,回答的人就會說“因為《老子》的哪段哪段是如何如何說的”,終歸還是擺脫不了語言文本,沒有放棄對資訊來源的追究,也就是說,沒做到“禪客相逢唯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的境界。[1]也許維特根斯坦說對了,語言的極限就是世界的極限。
而在形而下的層面來說,問題又要分成兩點。
(1)首先要承認語言確實是一種很有局限性的工具,凡有描述,必有遺漏,就像任何一份中國地圖也不可能“完整地”描述出中國是什麼樣子。——不過我們也得看到事情的另一面:沒有人會需要一份比例尺是一比一的地圖。
萊布尼茨以為,我們的語言是依賴於知覺的,因此知覺所具有的模糊、歧義等缺陷,同樣也表現在語言上。正是基於這個考慮,他才致力於發明一種“清晰的”符號體系,以使所有的問題都可以像數學題那樣得到解決。但是很遺憾,我們恐怕看不到這一偉大想法的成功希望了。
(2)其次,用世俗的眼光來看,《老子》的內容並沒有深奧到言語無法表達、邏輯無法梳理的程度,它之所以難懂,只在於年代久遠、材料匱乏。所以,不止是一部《老子》難懂,《論語》也難懂,《詩經》也難懂,《尚書》更難懂。胡適當年就說,“今日提倡讀經的人們,夢裏也沒有想到五經至今還只是一半懂得、一半不懂得的東西”;王國維這樣的大家也坦然說《詩經》他不懂的有十之一二,《尚書》他居然有一半都看不懂。(《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
————————
(1) 另一方面,作為儒家一系的《周易•系辭》雖然也說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卻認為聖人的意思借由卦、象和系辭被“完整地”表達了出來,而《老子》卻沒有給出一套類似於卦象的東西。但無論是卦是象,仍然都是人類表達意義的符號,也就可以和語言一起被劃入符號學的研究物件裏。
難處雖大,難點雖多,但好在學術是不斷進步的,這些年的出土新材料又這麼多,雖然又帶來了很多新問題,但一些橫亙千年之久的老問題總算陸續被解開了。那麼,那個神秘的“道”,終於能被說清了嗎?
即便只從日常生活來看,不但“道”說不清,很多平凡細碎的事情也一樣說不清。想像一下,你向全世界最好的畫家描述你最熟悉的一位元朋友,請畫家根據你的描述為你的這位朋友畫一幅肖像,他的畫可以逼真到何種程度呢?
任憑你千言萬語,你的描述也無法窮盡你這位朋友的所有特點。但令人欣慰的是,八九不離十的描述總還是可以做到的。同樣地,老子對他心目中的“道”也作過這樣一種約略的描繪: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曒,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複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執古之道,以禦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老子》通行本第十四章)[1]
————————
[1] 本書正文引述之《老子》通行本(八十一章本),以王弼本為底本,主要依陳鼓應先生《老子注譯及評介》所作的校訂。
陳鼓應先生的翻譯是:“看它看不見,名叫‘夷’;聽它聽不到,名叫‘希’;摸它摸不到,名叫‘微’。這三者的形象無從究詰,它是混淪一體的。它上面不顯得光亮,它下面也不顯得陰暗,它綿綿不絕而不可名狀,一切的運動都會還回到不見物體的狀態。這是沒有形狀的形狀,不見物體的形象,叫它作‘洸惚’。迎著它,看不見它的前頭;隨著它,卻看不見它的後面。把握著早已存在的‘道’,來駕馭現在的具體事物。能夠瞭解宇宙的原始,叫做‘道’的規律。”(《老子注譯及評介》)
既然“道”是無法言說的,這些描述便當然只是“道”的一點模糊的輪廓和模糊的感覺。但這裏還有一點訓詁上的爭議——李零先生重新校訂了文本,重點是把“執古之道”改作“執今之道”,論述說:“我們跟在它的後面,順著看,看不見它的尾巴;我們跑到它的前面,迎著看,又看不見它的頭。它是一條線索。我們用今天的道,觀察今天的世界,才能知道古代的事情,這就是所謂‘道紀’(道是貫穿古今的一條線)……‘執今之道,以禦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這段話,帛書本和今本不一樣,帛書本的意思是,既然道這個東西,‘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過去和將來,兩者都很難知道,就必須從今天人手。只有用今天的道理弄清今天的事情,然後才能知道古代是什麼樣,原來是什麼樣。今本把‘執今之道’改為‘執古之道’,其實是竄改。這等於說,只有以古禦今,才能懂得今。我看還是帛書本更好。”(《人往低處走》)
“道”就是混混沌沌、神龍不見首尾的這個樣子,[1]《老子》到底要人“執古之道”還是“執今之道”呢,到底要人以古禦今還是以今推古呢?若依我看,還是前者更加站得住腳。為什麼這樣說呢?——這要從《老子》這一章裏的“道紀”談起。
所謂“道紀”,陳鼓應先生釋作“道的規律”,李零先生則以為是“道是貫穿古今的一條線”,這兩種解釋恐怕都不準確。
————————
[1] 可以參照的是,《莊子•天運》描寫黃帝在原野上奏起《咸池》之樂,從上下文推斷,這裏的樂聲就是對“道”的一種隱喻:黃帝用陰陽的和諧來演奏,用日月的光明來照耀,聽者於是乎“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
《說文解字》:“統,紀也。”釋“紀”為“絲別也”;段玉裁注釋說:每根絲線都有個線頭,這就是“紀”,一堆絲線都把線頭束起來,這就是“統”。《淮南子•泰族》有一處“統”、“紀”連稱,頗能說明問題:“繭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這是在說人性需要加以引導的道理,用繅絲來作比喻,說蠶繭是可以從中抽絲的,但如果不經過女工用開水煮熬,抽出蠶繭的“統紀”,那是怎麼也抽不出絲線的。
這個“統紀”的意思就很明顯了,是指絲線的線頭。那麼“道紀”也就該是道的線頭,即《老子》本章所謂的“古始”(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我們可以把它領會為道之原,或者道之本。這樣理解,既有訓詁上的妥帖依據,上下文也變得暢通無礙了。[1]
魏晉玄學時代的天才少年,古代最著名的《老子》注釋家王弼說過,《老子》之書,如果一言以蔽之,核心思想不過是四個字:“崇本息末”。再具體一點來講,就是“觀其所由,尋其所歸,言不遠宗,事不失主”。(《老子微旨略例》)也就是說,《老子》之道如果可以比喻為種樹的話,就是要人多在樹根上下工夫,而不要總是把心思花在枝枝葉葉上。
王弼這個歸納即便在今天看來仍然不錯,“道紀”自然也是從根源上人手,“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更像是對道的狀態的描述,渲染它那神龍不見首尾的姿態,而不必把“隨”與“迎”從字面上引申到僅僅是時間層面上的“過去和將來”,何況這種引申在語法上也得不到足夠的支持。
————————
[1] 另一個可以參考的例證是《莊子•達生》的“而藏乎無端之紀”。馬敘倫說“紀”借為“基”,被陳鼓應在《莊子今注今譯》裏采信。但是,這個假借關係本身雖然成立,用在這裏卻多此一舉。所謂“無端之紀”,也就是“無端之端”,既合訓詁,又可以順暢地貫通上下文。
在《老子》那裏,“道”,就是萬事萬物的本源,而我們仍然可以沿用種樹那個例子,培其本自然可以育其末,事半而功倍,枝葉就算得不到任何照顧也會長得很好;但如果反過來搞,就會事倍功半,甚至招災惹禍。從這個意義上看,自然應該是“執古之道,以禦今之有”,要人以“道”統禦萬物,而不是“執今之道,以禦今之有”。——在王弼那裏,這並不是一個或此或彼的問題,因為“古今通,終始同;執古可以禦今,證今可以知古”,這就是《老子》所謂的“常”。(《老子微旨略例》)
王弼也是易學專家,喜歡援《易》人《老》。在他看來,《老子》與《周易》是相通的,《老子》的核心是“崇本息末”,《周易》的核心是“執一統眾”,政治就應該這麼搞。馬王堆帛書《十大經•道原》也說:“得道之本,握少以知多;得事之要,操正以正奇”,這是道家黃老一系的政治要領。
這話說得好像有一點形而下了,失去了《老子》的神秘光環。不過,在進入《老子》文本之前,有必要瞭解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老子》並不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哲學著作,它重點關心的並不是宇宙生成論或者本體論之類的問題,而是政治哲學(或者說是為政之道)的問題,它的進言物件也不是官僚或者百姓,而是國家統治者,也就是《老子》常常提到的“聖人”。
那麼,怎樣才能把政治搞好呢?把握“道紀”,也就是王弼所謂的“崇本息末”,表面看來是以古禦今,實際卻是以本禦末,以“合於道”的政治方針來統禦萬民。——儒家和道家都講無為而治,而這裏正是儒、道兩種無為方案的區別所在:道家的無為在於“崇本息末”,也就是“動于本,成於末”;而儒家的無為則是“動于近,成於遠”。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方略,同名而異實,然而有些學者把這兩種無為混為一談了,以至於認為《論語》裏的無為之道是被後人增竄而來的。
《呂氏春秋•先己》談到孔子論詩,《詩》曰:“執轡如組”,孔子說:“把這句詩搞明白,就足夠治理天下了。”——“執轡如組”於《詩經》凡兩見,一是《邶風•簡兮》,二是《鄭風•叔于田》,意思是說:駕車時握著韁繩就像編織絲帶一樣。
對孔子的話,子貢答了一句:“照這個意思,也太急躁了吧!”
子貢大概是覺得駕車也好,編織絲帶也好,手上總也不得停歇,難免有急躁之嫌。這種引申其實也很有道理,但顯然不是孔子所要表達的意思。孔子說:“這句詩不是在說駕車的人動作急躁,而是以編織絲帶為喻:絲線在手上打轉,花紋在手外成型。同樣地,聖人修身而大業成於天下。所以子華於說:‘丘陵成形了,穴居動物就安生了;江河成形了,魚蝦就有地方安生了;松柏茂盛了,旅人就有地方歇腳了。’”(《呂氏春秋•先己》)
《毛詩》闡釋這個絲帶的比喻,說“動于近,成于遠”,鄭玄說這是“禦眾之德”,按現在的學科劃分屬於組織行為學。這個意思很像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但運籌帷幄還屬於“有所為”,是在帷幄之中處心積慮地要想出具體的對策來“決勝千里之外”,而孔子的意思則近乎於“無所為”,並不是針對什麼具體事情來思考具體辦法,而是沒有什麼具體目的地關起門來修身——天下事紛紛擾擾你不用去操心,只要踏踏實實地把自身修養提高了,天下自然就會安定。這一邏輯,至少直到明清時代還被官方沿襲著。
孔子講的東西總是切中現實政治,老子也是一樣,他們縱然談論玄而又玄的天道,標靶也是近而又近的人事,儘管我們總是把老子想像得更加玄妙而高遠。
《老子》既然有特定的讀者物件,有特定的內容針對性,那麼,作為平頭百姓的我們自然也不妨旁聽一下。雖然《老子》的“道”恍惚混沌、不見首尾,但這應該不會構成多大的閱讀障礙,因為它的核心內容並不是這些,而是實實在在的、能被當時的統治者們聽懂的政治方略。
所以,“道”,慢慢說,應該還是可以說說的吧?
但我知道,很多人還是願意相信“道”是講不出的,老子之所以寫下五千言,只是因為他在一次出關的時候,被守關人看出了他身上的不凡之氣,硬逼他寫下點什麼。——這是一個流傳很廣、涵義很深刻的傳說,唯一的遺憾就是與事實不符。那麼,我們就從這個傳說開始講起吧。
您的評論: 注意: 評論內容不支持HTML代碼!
顧客評分: 差評 好評
請在下框輸入驗證號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