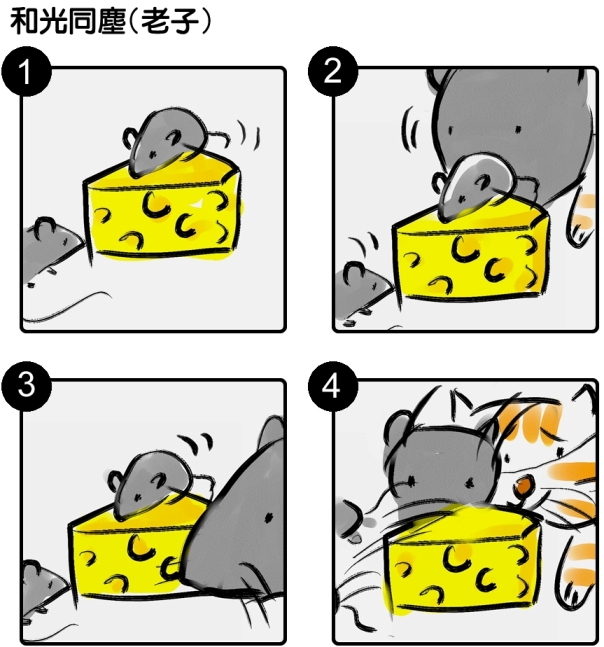列子(景中譯注)
 |
|
《列子》一書,《漢書•藝文志》道家類著錄《列子》八篇,班固自注曰:“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到唐天寶元年(西元742年),唐玄宗下旨設“玄學博士”,把《列子》等四部道家著作並列為經典,作為學子應試科舉的必讀書。《列子》當時被尊奉為《沖虛至德真經》。不久,柳宗元、高似孫相繼提出《列子》之偽,之後應者雲起,《列子》遂判為偽書;甚至連《列子》的題名列禦寇也被否定,高似孫的《子略》雲:“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於是列子便歸於不曾存在的神怪杜撰之列。近人梁啟超、郭沬若、楊伯峻、嚴北溟諸學者均支持《列子》偽書之議,似乎已鹹定論。既然是偽書,就要找出作偽者,先是說《列子》作注的張湛是作偽者,但因證據不足,又認定作偽者為王弼,又由於證據不足,便改為系出於魏晉人之手。
因為給《列子》定為偽書,畢竟缺乏鐵的證據,且不乏推測之辭,不能自圓其說,所以有學者開始質疑“偽書說”。並響亮提出《列子》不偽的觀點。如岑仲勉、李養正、日本學者武義內雄、臺灣學者嚴靈峰、陳鼓應便提出了有力的反駁意見,扭轉了《列子》“偽書說”邊倒的局面。本書贊成岑仲勉諸學者的意見,《列子》為偽書的案應予改判。《列子》是先秦子書,列子其人並非鴻蒙、列缺一類神怪,實有其人。《列子>>雖然記載了列子身後事,但這和《論語》、《莊子》也同樣記載了他們的身後事一樣,不能因此斷定它們都是偽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句公允的評介說:“此書皆稱‘子列子’,則決為傳其學者所追記,非禦寇自著。其雜記列子後事,正如《莊子》記莊子死,《管子》稱吳王西施,商子稱秦孝公,不足為怪。”既然是追記列子的言事,那麼《列子》反映了列子的思想體系是不會有錯誤的。
列子是鄭國人,生活在戰國時代,先於莊子。《莊子》中有二十二處提到列子,此外,《戰國策》、《屍子》、《呂氏春秋》等書也提到過列子。《屍子》、《呂氏春秋》中都講“列子貴虛”。《呂氏春秋•觀世篇》說:“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高誘注:“子列子,禦寇,體道人也。著書八篇,在莊子前,莊子稱之。”與班固的說法相同。列子是一位隱者,有他的老師、學友、弟子,雖窮卻不肯出仕而“為有國者所羈”。他崇尚清靜無為,養性體道,“心凝形釋,內外盡矣”,呈現出“在德機”、“衡氣機”、“太沖莫脫”的形象,當為辟穀、導引、入定功夫的先行者,因此,後來道教奉《列子》為圭臬,不認為《列子》“迂誕恢詭”,而認為它默察造化消息之運,發揚黃老之幽隱,簡勁宏妙,辭旨縱橫,因此,撰作道書,多所融攝,成為道教義理不可分之部分。不僅道教吸納《列子》思想體系,而且《列子》在中國哲學發展史上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貢獻之一,《列子》從世界本體、宇宙生成和物種轉化角度闡明了“道”的性質,形成了獨特的天道自然觀。提出客觀世界存在著統一的本質和規律,它本身無形無象,神秘莫測,無增無減,獨立不改。它不被他物產生,而能產生他物;它本身不變化,而能使天地萬物發生變化;它比任何具體事物及其具體的變化更具有主宰性,從而成為天地萬物產生和變化的總根源。它就是“道”。以此為基礎,《列子》的作者提出了宇宙生成的過程,闡明了“道”與“物”的關係,指出“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複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道與氣的統一,對道的物質屬性作出了明確的規定,豐富發展了老子道的本體論,使道的物質性及變化發展迴圈規律更加清晰。
貢獻之二,在繼承前代哲學中的辯證法思想基礎上,使其辯證法思想達到前所未有的水準。《列子》在《天瑞篇》中指出:“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于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在《莊子•秋水篇》中也有類似觀點:“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蔭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他們都認識到運動的普遍性和迴圈連續性,把整個運動看作是一個不斷的、無始無終的過程。在此基礎上又把中國哲學中運動理論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列子•湯問篇》指出:“無則無極,有則無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複無無極,無盡之中複無無盡。無極複無無極,無盡複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這樣便把宏觀世界的無限,微觀世界的無盡統一在物質的基礎上。完善了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的命題,提出了宇宙結構的層次及運動變化的無窮無盡性、物質性,把中國古代辯證法哲學提高到相當高的水準。
貢獻之三,《列子》提出自然命運決定論,比天帝決定命運的宿命論更為進步。先秦儒家的“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命是天命,天是上帝,在這種天帝命定論面前。人只能樂天知命,安於天命的主宰,順從上帝的安排。《列子》提出人力不可與命運相爭,命運決定人的壽天、窮達、貴賤、貧富,不是人力所能制約的。“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幹,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氣,平之寧之,將之迎之。”天道決定生死命運,只能順迎,不可干犯。儒家主張人聽命上帝的主宰,列子認為人應遵循天道自然規律。這是兩者的根本區別。此外,還有一點不同,那就是列子的命定論不排斥人在自然規律面前主現能動性,認為人可以認識社會的時勢和自然的機運,人掌握不掌握時勢和機運,其命運就會有不同的結果。列子指出人只有經過實踐才能認識自然規律。達到對至道的直覺體驗,辦事做到熟能生巧,方臻與道神契的境界,《列子》中“梁鴦飼虎”、“呂梁濟水”、“觴深操舟”等故事就是講人認識自然規律取得鹹功的事例。又如在《說符篇》中對盈氏二子、牛缺、宋國蘭子等人的遭遇指出:“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人的主觀能動性體現在知時,“昏昏味昧、紛紛若若”,就是“不知所以然而然”。世人有的年紀相仿、資歷相仿、才能相仿、容貌相仿,但壽天懸殊、貴賤懸殊、名譽懸殊、愛十曾懸殊,“成之幹道,命所歸也”;“死生自命也,貧窮者自時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又在《天瑞篇》中說:“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這裏強調人在自然規律面前做到無為無不為:無為知命,不與道抗爭;安時有為,認清時勢、掌握事物運動的規律和時機,就可以爭取到奸的結果。這是與宿命論的本質區別。“愚公移山”的寓言說明只有正確認識客觀事物與人的關係,人才能改變環境,創造奇跡。山不再增長,而人子子孫孫卻可以無窮盡地延續增長;無限可以戰勝石限,因此只要下定決心就可以做到移山。“夸父追日”的寓言告訴人們不能正確認識自然與人的關係,恃強蠻幹,勢必失敗。可見成敗命運皆在命定之中,又在“知命安時”的運作之中。
貢獻之四,在闡明貴虛、內觀、生死、幻夢諸問題上皆有新意。貴虛是道家基本哲學思想,老子講:“致虛極,守靜篤”,認為虛無不受,靜無不待,道興無為,虛無自然,名為得道。《列子》全書都貫穿貴虛思想,張湛在麼列子序》中指出:“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下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與肆任;順性則所以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列子崇尚自然,認為一切都在不停地幻化之中,瞬息盈虧,暗中移易,終究歸於寂滅,一切皆虛,無所謂生死、有無、是非、成敗,順自然之性,持虛靜,便是與道合一。所以列子說:“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也。事之破 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複也。”虛,就無所謂貴賤,保持清靜虛默,不競世俗之名利,就是得到了“道”。《列子•仲尼篇》在堅持虛靜宗旨的基礎上,提出了“內觀”說:“務外遊,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于身,遊之至也;求備子物,遊之不至也。”“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視。物物皆遊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遊,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遊其至矣乎!遊其至矣乎!”這裏的內觀,就是修心,修心就是修道,道常靜虛,心守靜虛,才能以心合道。所以說內觀取足於身,才是最完備的觀萬物,只有內觀才能“物物皆遊”。靜與虛是統一的,能靜始能悟虛,悟虛才能靜定。靜定則欲不生,欲既不生,則為真虛真靜,才能漸入真道。這就是列子修身體道的基本途徑。
基於貴虛,列子又提出自然生死觀,指出生與死是自然規律,不曾有生,也不曾有死。《天瑞篇》說:“道終平本無始,進平本不有。有生則複於不生,有形則複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止其終,惑於數也。”“死之於生,一往一返。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相若矣。”《仲尼篇》又說:“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生死是常理,生死與道相依。該生的而生存著、該生的卻死掉了,都是符合道的規律的;該死的死了,該死的卻活著,也都是自然規律的體現。“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這種把生死視為陰陽之變,氣之幻化的觀點,揭開了關於生與死的神秘面紗。列子還指出,生命是短暫的,不必計較何時死,而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就是率性而為,不要委屈自己,可以從心所欲,或享樂自己的財產,或散盡家產,不必計較身後名聲。堯、舜、桀、紂生前名聲不一,但死後都變為腐土,歸於自然。
《列子•周穆王篇》有八個故事講丁關於幻與夢的問題,旨在說明世界萬物都是虛妄不實、如夢如幻。穆王西遊,說明了“變化之極,徐疾之間”便可完成。若役夫“苦則苦矣,夜夢為人君,其樂無比”;尹氏“心營世事,鐘慮家業,心形俱疲”,“夢為人僕,超走作役,無不為也”,說明苦逸相反復。樵鹿相爭,說明覺夢難辨。華子患失憶症為返樸歸真,認為病癒,反而“擾擾萬緒起”,被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心。“古莽”三國對夢覺的感受各異,有的以覺為實,夢為虛;有的以覺為虛,夢為實;有的常覺不眠,無夢,都是民俗習慣和鹹見。凡此種種,說明造物者難窮難盡,因形者隨起隨滅,後者相對於前者即為幻化。因此,不要為事物的表面現象所迷惑。為了說明幻夢之間的關係,列子對夢的成因作了深入解釋,提出“神遇為夢,形接為事”,夢是精神活動,事是形體與外物的接觸。晝思夜夢,形神所遇,夢以事為根源,是以一定的生理、心理變化為根據而產生形形色色的夢。這種解釋幾近于現代科學對夢的解釋。
《列子》還有許多成就值得稱讚,值得研究,就是上述幾點淺見也尚待專門研究,這裏不便深究。
《列子》一書西漢末尚存完篇,因世事變動幾近亡佚。永嘉之亂,張湛家與王弼家一起逃難江南,張湛曾在王弼家的藏書中挑選了一批罕見書帶著南行。後來張家在帶去的書中發現了《列子》一書三卷,張湛又在他處尋得其他篇,合輯為八篇足數,遂加以作注。張湛之後又有唐人殷敬順撰《列子釋文》。清人汪繼培對張、殷二書加以校訂,刊入湖海樓叢書。此外,四部叢刊、諸子集成諸叢書亦有刊行《列子》其書者。這當中,張湛收集《列子》殘篇、並為主作注,對保存、傳播中國古代典籍功不可沒。
今人楊伯峻有《列子集釋》,此外,嚴北溟、陳鼓應、岑仲勉等也有專書及論文對《列子》進行了有價值的研究。
本書以諸子集成刊本為底本,在撰寫中參閱了上述著作及論文,參互對比,取長補短,參以己見,特別是《列子》一書的真偽及思想等問題,分歧較大,本書只作簡要表達,不作專門考辨,注釋、譯文的不同見解,也只是寫明己見,未注明分歧意見何在,不妥之處,敬請指正。
您的評論: 注意: 評論內容不支持HTML代碼!
顧客評分: 差評 好評
請在下框輸入驗證號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