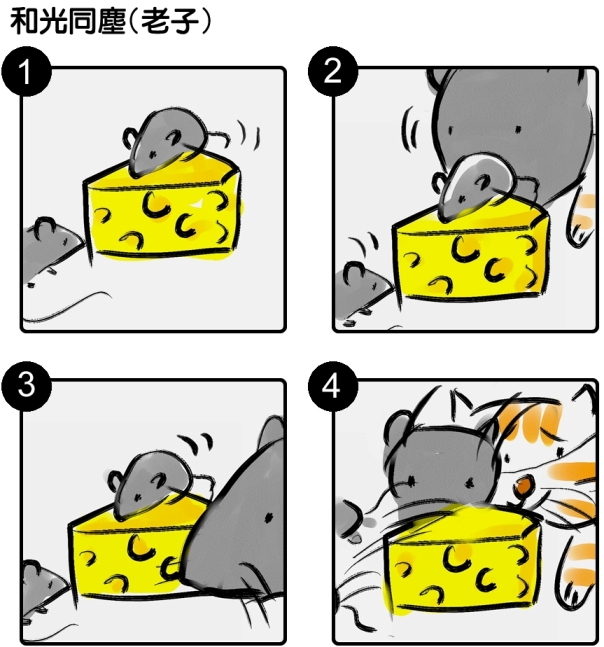民眾信仰的陰面和陽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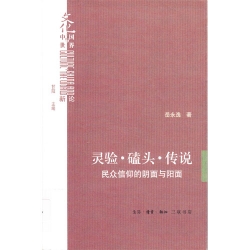 |
|
序言:
百年前,梁啟超曾提出“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以及“世界之中國”的說法。進入21世紀以來,關於“世界之中國”或“亞洲之中國”的各種說法益發頻頻可聞。
但所謂“中國”,並不僅僅只是聯合國上百個國家中之一“國”,而首先是一大文明母體。韋伯當年從文明母體著眼把全球分為五大歷史文明(儒家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教文明)的理論,引發日後種種“軸心文明”討論,至今意義重大。事實上,晚清以來放眼看世界的中國人從未把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簡單看成是中國與其他各“國”之間的關係,而總是首先把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看成是中國文明與其他文明特別是強勢西方文明之間的關係。二十年前,我們這一代人創辦“文化:中國與世界”系列叢書時,秉承的也是這種從大文明格局看中國與世界關係的視野。
這套新編“文化:中國與世界”論叢,仍然承繼這種從文明格局看中國與世界的視野。我們以為,這種文明論的立場今天不但沒有過時,反而更加迫切了,因為全球化絕不意味著將消解所有歷史文明之間的差異,絕不意味著走向無分殊的全球一體化文明,恰恰相反,全球化的過程實際更加突出了不同人民的“文明屬性”。正是在全球化加速的時候,有關文明、文化、民族、族群等的討論日益成為全球各地最突出的共同話題,既有所謂“文明衝突論”的出場,更有種種“文明對話論”的主張。而晚近以來“軟實力”概念的普遍流行,更使世界各國都已曰益明確地把文明潛力和文化創造力置於發展戰略的核心。說到底,真正的大國堀起,必然是一個文化大國的崛起;只有具備深厚文明潛力的國家才有作為大國堀起的資格和條件。
哈佛大學的張光直教授曾經預言:人文社會科學的21世紀應該是中國的世紀。今日中國學術文化之現狀無疑仍離這個期盼甚遠,但我們不必妄自菲薄,而應看到這個預言的理據所在。這個理據就是張光直所說中國文甽積累了一筆最龐大的文化本錢,如他引用Arthur Wright的話所言:“全球上沒有任何民族有像中華民族那樣龐大的對他們過去歷史的記錄。二千五百年的正史裏所記錄下來的個別事件的總額是無法計算的。要將二十五史翻成英文,需要四千五百萬個單詞,而這還只代表那整個記錄中的一小部分。”按張光直的看法,這筆龐大的文化資本,尚未被現代中國人好好利用過,因為近百年來的中國人基本是用西方一時一地的理論和觀點人看世界,甚至想當然地以為西方的理論觀點都具有普遍性。但是,一旦“我們跳出一切成見的圈子”,倒轉過來以中國文明的歷史視野去看世界,那麼中國文明積累的這筆龐大文化資本就會發揮出其巨大潛力。
誠如張光直先生所言,要把中國文明的這種潛力發柞出來,我們需要同時做三件事,一是深入研究中國文明,二是儘量瞭解學習世界史,三是深入瞭解各種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理論,有了這三個條件我們才能知所辨刈。做這些工作都需要長時間,深功夫,需要每人從具體問題著手,同時又要求打破專業的壁壘而形成張光直提倡的“不是專業而是通業”的研究格局。這套叢書即希望能朝這種“通業研究”的方向做些努力。我們希望這裏的每種書能以較小的篇幅來展開一些有意義的新觀念、新思想、新問題,同時叢書作為整體則能打破學科專業的籬笆,溝通中學與西學、傳統與現代、人文學與社會科學,著重在問題意識上共同體現“重新認識中國,重新認識西方,重新認識古典,重新認識現代”的努力。
之所以要強調“重新認識”,是因為我們以往形成的對西方的看法,以及根據這種對西方的看法而又反過來形成的對中國的看法,有許多都有必要加以重新檢討,其中有些觀念早已根深蒂固而且流傳極廣,但事實上卻未必正確甚至根本錯誤。這方面的例子可以舉出很多.例如,就美術而言,上世紀初康有為、陳獨秀提倡的“美術革命”曾對20世紀的中國美術發生很大的影響,但他們把西方美術歸結為“寫實主義”,並據此認為中國傳統美術因為不能“寫實”已經死亡,而中國現代美術的方向就是要學西方美術的“寫實主義”,所有這些都一方面是對西方美術的誤解,另一方面則是對中國現代美術的誤導。在文學方面,胡適力圖引進西方科學實證方法強調對文本的考證誠然有其貢獻,但卻也常常把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引入死胡同中,尤其胡適頑固反對以中國傳統儒道佛的觀點來解讀中國古典文學的立場更是大錯。例如他說“《西遊記》被三四百年來的無數道士和尚秀才弄壞了”,認為儒道佛的“這些解說都是《西遊記》的大敵”,但正如《西游記》英譯者余國藩教授所指出,胡適排斥儒道佛現在恰恰成了反諷,因為歐美日本中國現在對《西遊記》的所有研究成果可以概觀地視為對胡適觀點的駁斥,事實上,“和尚,道士和秀才對《西遊記》的瞭解,也許比胡適之博士更透徹,更深刻!”
同樣,我們對西方的瞭解認識仍然遠遠不夠。這裏一個重要問題是西方人對自己的看法本身就在不斷變化和調整中。例如,美國人曾一度認為美國只有自由主義而沒有保守主義,但這種看法早已被證明乃根本錯誤,因為近幾十年來美國的最大變化恰恰是保守主義壓倒自由主義成了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這種具有廣泛民眾基礎而且有強烈民粹主義和反智主義傾向的美國保守主義,幾乎超出所有主流西方知識界的預料,從而實際使許多西方理論在西方本身就已黯然失色。例如西方社會科學的基本預設之一是所謂“現代化必然世俗化”,但這個看法現在已經難以成立,因為正如西方學者普遍承認,無論“世俗化”的定義如何修正,都難以解釋美國今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自稱相信宗教奇跡、相信上帝的最後審判這種典型宗教社會的現象。晚近三十年來是西方思想變動最大的時期,其變動的激烈程度只有西方17世紀現代思想轉型期可以相比,這種變動導致幾乎所有的問題都在被重新討論,所有的基本概念都在重新修正,例如什麼是哲學,什麼是文學,什麼是藝術,今天都已不再有自明的答案。但另一方面,與保守主義的崛起有關,西方特別美國現在日益呈現知識精英與社會大眾背道而馳的突出現象:知識精英的理論越來越前衛,但普通民眾的心態卻越來越保守,這種基本矛盾已經成為西方主流知識界的巨大焦慮。如何看待西方社會和思想的這種深刻變化,乃是中國學界面臨的重大課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今天我們已經必須從根本上拒斥簡單的“拿來主義”,因為這樣的“拿來主義”只能是文化不成熟、文明不獨立的表現。中國思想學術文化成熟的標誌在於中國文明主體性之獨立立場的日漸成熟,這種立場將促使中國學人以自己的頭腦去研究、分析、判斷西方的各種理論,拒絕人云亦云,拒絕跟風趕時髦。
黑格爾曾說,中國是一切例外的例外。近百年來我們過於迫切地想把自己納入這樣那樣的普遍性模式,實際忽視了中國文明的獨特性。同時,我們以過於急功近利的實用心態去瞭解學習西方文明,也往往妨礙了我們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文明內部的複雜性和多樣性。21世紀的中國人應該已經有條件以更為從容不迫的心態、更為雍容大氣的胸襟去重新認識中國與世界。
承三聯書店雅意,這套新編論叢仍沿用“文化:中國與世界”之名,以示二十年來學術文化努力的延續性。我們相信,“文化”這個概念正在重新成為中國人的基本關切。
导言:
2008年6月,正是中國內地高校的“忙月”。就在這個忙月,華北腹地小鎮范莊的武文祥老人不幸逝世。雖然是高校的忙月,但在這個月的13曰,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大學、中國農業大學等相關的系所以及中國民俗學會還是派專人前往北京七百餘裏之外的范莊,參加了武文祥老人的葬禮,並敬獻了挽聯和花圈,以表達對老人的哀悼和敬意。
2009年2月25日清晨,在武文祥老人兒子的陪伴下,好幾個說著普通話,明顯是外地來的人肅立在武文祥老人的墳頭.來自北京師範大學的劉鐵梁教授沉重而不乏親切地說:“武老師,您可好?我,劉其印,還有,……我們來看您啦!”
武文祥這個生活在華北腹地小鎮、名不見經傳的老人是誰?在其逝世後,數百里之外京城、省城的學者何以會千里迢迢地來憑弔他?當下差距既在縮小也在擴大的城市和鄉村、知識精英和鄉民為何相識?又是如何交往、溝通與理解的?
上述這些看似原本不應該發生關係的關係,都源自范莊這個小鎮每年二月二例行舉辦的龍牌會這個有著濃厚傳統色彩,並集祀神、跪拜、娛樂、人際交往、商品交易於一體的鄉村廟會。武文祥原本是這個小鎮學校的老師,並從校長任上退休。退休後,差不多從1991年開始,隨著龍牌會的“復興”,作為地方上的文化人,武文祥就接受了龍牌會會首和范莊村委、村政府的共同邀請,在每年龍牌會期間負責外事工作,專門接待從京城、省城甚至海外來的研究者、媒體記者等尊貴的客人。於是,近十多年來中國人文社會學界一些熟悉的名字,劉其印、劉鐵梁、高丙中、王斯福、王銘銘、周星、郭于華、莊孔韶、趙世瑜、劉魁立、宋兆麟、陶立墦、祁慶富、葉濤、趙旭東等等,都與這位樸實、和善的鄉村老人聯繫在了一起,有著或疏或親、或多或少的聯繫。
范莊龍牌會究竟是一個怎樣的鄉村廟會?它承載、表達著怎樣的民眾信仰?言說著華北腹地鄉民怎樣的心性、習慣,世界觀或者說文化觀念?它是怎樣適應著當下的社會,並日漸興旺,直至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大潮中的弄潮兒?國內外學界已經熟悉的,源自西方基督文明的神聖一世俗、狂歡一日常的二元話語和彌散型宗教、世俗化宗教、神鬼祖先、帝國的隱喻、朝聖等理論范式對華北腹地這個有代表性的鄉村廟會是否同樣適用?具有普適性?清末以來,與神神、廟宇相關聯的敬拜長期被主流話語貼上了迷信、陋習等標籤,與孔孟之道,四書五經一同被視為是民族落後挨打的誘因之一,是統治者以及智識精英一直努力打壓、改造和利用的對象。但是,生活在華北腹地的這些鄉民似乎有著當政者難以想像的韌性,不但祖輩傳承的信仰未曾斷絕,就連在公共空間的群體祭拜等祭祀活動也見縫插針式地舉行,直至在20世紀晚期處處花開。顯然,這完全不是因為早已經使用化肥、農藥和其他科技手段進行生產,也使用電話、手機、冰箱等電器,生病也會上醫院的鄉民的“愚昧”。那麼,繁雜的中國民眾信仰,以神神、香燭紙炮、磕頭、看香、許願還願和行好為表徵,以靈驗為核心,此起彼伏的鄉村廟會的生機究竟在哪里?是否有新的解讀視角?這些長期被定性為負面的、陰性的和消極的傳統與當下的新農村建設、和諧的鄉村發展是否存在良性互動的可能?當政者、智識精英究竟應該有一種怎樣的理性的態度?是要高高在上的,貌似親民為民著想的“眼睛向下看”,還是要首先真正地尊重並平心靜氣地瞭解這些風俗習慣的“平視”?
這些都是這本小書關注並試圖回答的問題。
最先激發我思考這些問題的,不是書本上被描述的經驗,也非層出不窮的理論,而是1999年的龍牌會現場。1999年3月15曰至19曰,在劉鐵梁教授的帶領下,我們師生一行四人對龍牌會進行了調查。當年前往龍牌會調查的還有當時仍在北京大學教學的周星教授和河北省民俗學會的劉其印等人。在上研究生之前,我一直生活工作在四川鄉村。雖然家鄉人至今都還在使用不少以廟、寺、觀等命名的地名,但從有記憶開始,故鄉並無人們趨之若鶩的大規模求神拜佛的廟會。唯一一個有些淵源和聲勢的梓潼七曲山大廟,也因為離家有八十裏地,而且很快就收昂貴的門票,貧窮的鄰居們也很少前往。當然,對家鄉的民眾信仰、廟會的陌生還受到不語怪力亂神的父親的影響。在離開四川之前,我長期也對廟、神、廟會敬而遠之。
正因為這樣,當我第一次在寒意十足的龍牌會現場,看到黑壓壓的人匍匐在簡易神棚內的龍牌等諸多神馬面前,耳朵充斥著嘶啞的廟戲聲音和驚天動地的鼓聲,眼睛也被神棚中的香煙熏得直流淚時,在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茫然了。在人流中被淹沒的,我第一感覺就是:這不是“封建迷信”嗎?今天的人怎麼還這樣?這是當政者一再宣導的要現代化、要科技要文明要發展的中國鄉村嗎?這個地方的人怎麼這樣愚昧?事實上,數年後,當看到我拍攝的范莊這一帶廟會的相片和影音檔時,我那些信仰基督教、天主教並對中國文化有著較多瞭解的外國友人情不自禁地問我:這是中國嗎?這不是偶像崇拜嗎?中國農村現在還這樣嗎?同樣,當我在課堂上給來自全國各地的80後、90後的大學生展示這些資料時,完全生活在都市里的朝氣蓬勃也無畏的學生不僅如同外國友人那樣認為這是愚昧、粗俗、落後、不可思議,個別人甚至懷疑我這些資料的真實性。
如今看來,十餘年前因文化偏見和自以為文明的我在龍牌會現場因驚訝、困惑而內心的發問極不正確。可是,也正是那些與我的外國友人和青年學生一樣的,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的文化偏見、陌生感以及驚訝激發了我近十多年來對自己長時間也接受認同的所謂愚昧、迷信和陋習的調查研究。為此,雖然我也讀書,也看前人的研究與理論,但這些已有的定論對我的衝擊力遠遠不如田野現場來得迅猛。
在1999年龍牌會現場,當我很快經歷文化陣痛和迷茫後,在明白自己是個學習者、研究者而非高高在上的審判者與批判者之後,我迅即展開了觀察和訪談。我發現,在神棚裏面人們對龍牌等神神虔誠地敬拜與讚美的同時,神棚外的不少人對龍牌有著不同的表述,還有不少人在我問及龍牌時閃爍其辭,並不前往敬拜,有的甚至閉口不談。於是,我對已有的關於龍牌會的研究文章常常提及的“范莊人”產生了疑惑,並進一步思考“民”的同質性的問題。也是在龍牌會現場,面對身穿制服前往燒香磕頭的員警,面對西洋鼓樂和傳統鼓樂、拉碌碡、雜技、魔術以及脫衣舞等同場競技的喧鬧,面對果樹種植的科技宣傳與看相算命卦攤的比肩而立,究竟是哪些因素參與建構和促生了今天的龍牌會?哪些是傳統的,哪些是現代的?傳統和現代、官與民、國家與社會、治與亂、科技與迷信、神與人、會頭與信眾、局內人與局外人等等,在這裏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關係?就如表面上看起來雜亂無序的龍牌會一樣,這些問題一股腦兒地向我湧來。第一次在龍牌會的那幾天,是充實的,也是愉快和痛苦的。
還是在田野現場,激發了我對在當地仍然存留的娃娃親這一不僅僅是婚姻慣制還與信仰關聯的生活習俗的思考。但對我這個已經在當地行走數年的他者而言,發現當地人不以為然、習以為常的這一習俗是在2002年。當年的7月7日(農曆五月二十七)至12日(農歷六月初三),我專程前往距離范莊不遠的C村(因為我行走的這一帶數十個村莊都以產梨為主,所以我常以梨區稱之),調查這裏的娘娘廟會,同行的有劉其印、當時在北京大學任教的趙旭東博士,以及我的學弟華智亞、薑炳國等人。當時,我們分頭住在村民家裏。由於我去得較早,我十分有幸地直接被廟會會長迎進了他自己的家中。會長有三個兒子,二兒子在外鄉工作,大兒子和三兒子留在村裏。當時,大兒子已經自修了新宅,會長夫婦與新婚不久的么兒子一同生活在老宅。我被安頓在心宅。與這一帶其他村子的廟會一樣,它為當下通訊手段多樣的鄉村提供了人與人,尤其是親戚鄉鄰之間面對面交往的時空。通常借廟會之機,出嫁到外村的女兒都會回娘家與親人團聚,也順帶燒香看梆子、墜子為主體的廟戲(有時也不乏現代歌舞)。當然,這也是喜歡熱鬧、自由的小孩子樂於經歷、體驗的時空。
7月9日(農曆五月二十九)是娘娘廟會的正日子,這天晚上的廟戲也一直唱到夜裏零點。我雖然早早回到住地,但天熱得厲害,難以入睡,於是索性坐在庭院裏乘涼。仰望星空,聽夜空中傳來的飄渺的唱腔,不用像白天那樣忙著觀察、筆記,別是一番享受。在廟戲快結束的時候,當天從鄰村回來的會長的閨女帶著她的兩個小孩到了新宅。在她給兩個小孩子洗刷的時候,我就與這位年齡顯然不太大的母親聊起天來。閒聊中,意外地發現我們倆是同年生人,但她的閨女已經十歲,兒子也六七歲了。在我說出自己還沒有物件並對她表示出羡慕、贊許之意時,這位爽朗的年輕母親對我說道:“我真不知道你們城裏人在想什麼,都這麼大了,怎麼還不結婚?”然後頭朝兩個孩子揚了揚,低聲對我說:“這兩個都已經訂婚了!”最後這一句讓我倍感驚訝,猶如四年前在龍牌會現場的我。我脫口而出:“真的?他們倆都訂了?你沒騙我吧?”“是呀,我們這裏都這樣,附近這一帶差不多都這樣,不信你去問問別人。所以你得抓緊,都三十多了,你也不小啦!”
在一定意義上,鄉下人是無法理解城裏人的,但對城裏人卻有著寬容與親切。可是,城裏人一直都是貶視鄉下人的,並不願置身於鄉下人的生活中來看鄉下人,有著貌似高貴的褊狹。文化差別、文化隔膜乃至文化敵視一直都存在於不同族群甚至不同群體和行業之間。鴉片戰爭以來,很多基於田野調查的海外中國研究確實不乏真知灼見,但其中也確實有不少對中國社會、歷史、文化、宗教、藝術等的認知夾雜著西方人骨子裏的高傲和偏見。
因為天熱而有的這次隨意閒聊,激發了我在隨後的日子對當地“娃娃親”的探究。但與四年前處於震驚和高高在上的褊狹不同,這次我研究的出發點是想找到之所以還這樣”的合理性。如同我在本書中描述分析的那樣,有著變異並將男女當事人推向前臺的當下梨區的娃娃親確實是既往婚俗的延續,但它也絕對不是機械的固守,而是與當下當地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與人們對生活世界的評判、期待有著緊密的關聯。更為重要的是,雖然梨區廟會現場的神馬前,我經常都看到年滿十二周歲的孩子在父母的帶領下的掃堂(壇)還願,但我並未將這些敬拜行為與娃娃親這一婚俗聯繫起來。直到2005年7月,當我在梨區段光和何計兩個家中過會的現場目睹眾多父母帶領孩子掃堂時,同樣是在與這些孩子都上過學的父母的閒聊中,我才猛然發覺這一似乎純然是處於信仰的還願行為與貌似保守的娃娃親這一婚信之間的緊密關聯。也就是面對這些在儀式中很少說話的“成人了”的十二歲的孩子,我才深切地理解馬塞爾•莫斯(Marcel Mauss)所言的“整體的社會事實(total social fact)”、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所編織出的“權力的文化網路”和柯利弗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所言的“解釋的解釋”。
不僅是娃娃親、廟會與神神,對村落廟會傳說和磕頭的解讀給予了我同樣的愉悅。強調靈驗,看似荒誕的傳說實則是鄉土社會流動的魂,是一個地方之所以成為一個地方的原因之一,是人們獲得認同、培養情操以及與他群交往的方略和手段。同樣,從日常生活層面的祖師爺信仰,我們會發現,很多年前就引發中西文明之間衝突並長期被基督文明貶斥的磕頭,這個刻寫中國人身體的基本動作與西方人的自詡為文明的鞠躬、擁抱、親吻等沒有任何兩樣,它同樣隱藏著理解和平等的訴求與基因。
在1948年出版的英文版《鄉土中國》(Earthbound China: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的結論部分,深受功能主義影響並享譽國內外的社會學大師費孝通有句名言:“社會學田野工作始於假設也止於假設”。在中文版《雲南三村》的“導言”中,費孝通重申了他曾經在英文版《鄉土中國》的導言和結論中強調過的上述觀點:在沒有理論引導時,實地調查所得到的材料是“零星的,沒有意義的”,而且還會埋沒“很多頗有意義的發現”。這種明確的要為農民服務,要為社會服務,要為國家服務,也要為理論建構服務的基本治學態度,或者是費孝通成為大師的關鍵所在,也導致了中國社會學注重實用的基本走向。但非常愧對大師的是,作為他著作的忠實讀者和他本人的敬仰者,我自己上述的田野調查顯然都沒有明確的假設也不是歸於假設的,常常不但貿然潛往,還經常都是從經驗中來到經驗中去。
當然,這種沒有明確目的和雄心的田野心態,或者也因為我研習俗學,而且是從感同身受的感受和體驗來研究民俗文化有關。雖然在官方調整來調整去的學科分類中,民俗學被歸屬了當下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顯赫的社會學門下,但對我而言民俗學依舊有著其個性;
它是一門向後看也必然充滿懷舊與傷感的學問,並自然而然地與民族主義、浪漫主義糾纏一處,但它也是從下往上看,天然有著批判性、反思性,從而謹慎甚至不合時宜的學問,因此也是最容易被邊緣化和工具化的學問。
您的評論: 注意: 評論內容不支持HTML代碼!
顧客評分: 差評 好評
請在下框輸入驗證號碼: